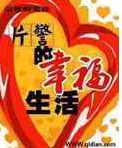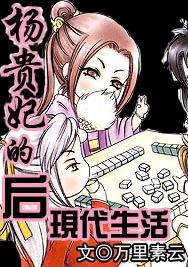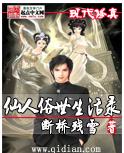文艺生活-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兴,需要一位有魄力的内行人来领导。
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矩。
在华国的电影圈,导演是剧组的核心,剧组里的成员要服从导演的安排,配合导演的工作,这就是电影圈的规矩。
姜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遭到剧组罢工,那是因为他没给人家工资。
韩三评当过导演,他明白在剧组里导演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在圈子里有句话,不骂人的导演不是个好导演。
这话有点偏颇,实际上也有不少好脾气的导演,不过这说明了导演在片场的地位。
在拍片的时候,导演骂你就要听着,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有事情可以私下沟通,和导演当场顶撞是圈子里的大忌,以后谁还敢用你。
韩三评知道这件事是京影厂的人做的差了,坏了规矩。
这帮人仗着出身京影厂,没把冯晓刚放在眼里,如果换一位京影厂的导演,他们就不敢这么做了,说到底还是欺生。
韩三评没想到的是林子轩说换人就换人了,干脆利索。
京影厂不会因为几个人就和林子轩闹翻,他们还没有那么霸道。
尤其是在目前的困境下,厂子缺少资金,很多片子没办法拍摄,同时也不能让厂子里的职工闲着,总要给他们安排事做,不然这些人又要闹事了。
韩三评来到京影厂不到三个月,基本上摸清了厂子的情况,只感觉焦头烂额,前路艰难。
当然,如果不是这么有难度的工作,也轮不到他来当这个副厂长了。
这次和好梦公司的矛盾只是一件小事,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林子轩挂了电话,同样不再想这件事,他要安排艺术中心的人进入冯晓刚的剧组。
选择的标准当然是熟人优先,尤其是跟着他一起到美国拍《京城人在纽约》的那批人,他们在美国一起吃住了半年的时间,非常了解各自的性格和特长,配合默契。
京城电视艺术中心这几年的效益很好,不断壮大,目前有接近两百人的规模。
在怀柔影视基地建设的时候,李虹在影视基地附近找了块地方建了一座三层的办公楼,艺术中心搬出了原来租住的四季青公社。
影视基地目前已经投入使用,艺术中心的电视剧都在那儿拍摄。
只是由于怀柔属于京郊,位置偏了点,影视圈的其他剧组不怎么愿意过去,如何推广和宣传是影视基地面临的问题。
不过这些不归林子轩管了,自然有其他人操心。
从艺术中心拉人很容易,冯晓刚写了一个名单,都是和他惯熟的人,用着放心。
李虹批准之后,这批人就会到《甲方乙方》的剧组工作,他们虽然没拍过电影,但都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应该能很快上手。
“这下行了,咱们自己人做事,进度能快上不少。”冯晓刚放心道。
“你多操点心,别让两帮人闹出矛盾来。”林子轩提醒道。
现在剧组里有一半是京影厂的人,一半是艺术中心的人,弄不好就会出事。
“放心吧,我和他们交待好了,咱们的人精明着呢,想要偷师就要和京影厂的人打好关系,等学会了就用不到他们了,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冯晓刚贼笑道。
“咱们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碰到认真做事的,主动投靠的,能拉拢的就拉拢过来,人才永远不嫌多。”林子轩深谋远虑道。
“林董英明!”冯晓刚拱手,装作仰慕状。
“冯总睿智!”林子轩接话道。
“彼此彼此。”两人同时笑着说道。
他们互相吹捧一番,觉得差不多了,也就该干嘛干嘛去了,主要是气氛不够,要是加上葛尤,三人能侃上个把钟头。
法国戛纳,葛尤在酒店里看杂志。
这是一本法国的电影杂志,上面有国外记者对于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各部片子的评论,还会给电影打分,分数越高的片子越受欢迎。
杂志是《活着》的投资商拿来的,据说《活着》在放映后分数很高,投资商很兴奋。
葛尤看不懂外文,就是没事的时候随便翻翻。
他不爱出去享受戛纳的阳光和沙滩,也不去看每天都在放映的各国优秀电影,其中不乏电影大师的作品,主要是他看不懂,连个翻译字幕和配音都没有。
也就是《活着》放映的时候他和投资商一起在影院里又看了一遍。
巩莉不同,电影节是女明星的秀场。
她就不会在酒店里呆着,要么和投资商一起找片商吃饭,要么就是出席一些展映活动,宣传一下电影,说几句漂亮话。
要在国外媒体上保持曝光度,这是成为国际影星的基本条件。
这让葛尤觉得特愧疚。
自己来戛纳没帮上什么忙,和人聊天都费劲,自个出去怕迷路,又不想麻烦别人,其他人都挺忙的,还是呆在酒店里好了,至少不给人惹麻烦不是。
他还记着一件事,就是那部叫做《京城的风很大》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自然没办法和《活着》相比,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才是记者们追逐的焦点,“一种关注”这个单元只有少部分人才会注意。
葛尤翻遍了杂志也没有找到有关纪录片的内容。
他虽然看不懂文字,却能看懂图画,如果这部纪录片大受欢迎,在报导上应该会出现林晓玲的照片,毕竟晓玲同学是其中的主演啊。
看来是没戏了。
事实上,这部纪录片在电影节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开来,被认为是华国新时代的电影。
以前,外国影人看到的华国电影要么年代久远,要么是反映偏远农村的片子,在国内这种做法被批判为“拍摄阴暗面迎合国外的评委”。
这部纪录片不同,它拍摄的是当下的华国,也不是农村,而是华国的首都。
它展现了1993年华国首都的真实面貌,让外国人看到了一个正在改变中的华国。(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八章青年们
这部纪录片给外国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让他们惊讶的是华国竟然有地铁,有豪华饭店,街道上有小轿车,有穿着时尚的女人,人们的精神面貌看起来不错,能看到不少正在施工的工地。
整座城市既显得古老,又充满了活力。
看过这部纪录片,有人询问曾经去过华国的电影人,这真的是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么?
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华国还是七十年代的模样,人们穿着相同的衣服,共同劳作,唱着革命歌曲,这就是以往华国的电影给他们的记忆。
华国的第五代导演都喜欢拍过去的时代,对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进行回顾和反思。
他们还喜欢拍偏远落后地区的电影,认为在苦难中才能展现人性。
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在城市里有吃有喝的人拍起来有什么意思,没有看点,只有那些在贫苦中挣扎求生的人才能让观众有所感触。
他们认为这就是艺术,艺术就应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这时候第五代导演的镜头总是避开繁华的都市,避开华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专注于描述苦难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这样的电影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认可,第五代导演屡屡拿到国际大奖。
在华国国内,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认为这是用华国的阴暗面来迎合西方社会的猎奇心理。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有人认为是艺术,有人认为是糟粕,不过这类电影的确对外国的观众产生了误导。
《京城的风很大》表现的是京城街头的景象,没有专门拍一些像故宫那样的旅游景点,也没有故意找社会上的阴暗面,采访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市民。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国外的电影人看到这个片子,觉得和正在戛纳广受好评的《活着》不同,这不同于华国以往的影片,是华国新时代的电影。
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团队则被称为华国电影的新生力量。
京城电影学院,贾章柯和同学从洗印厂看电影回来。
提起洗印厂,一般是指位于北太平庄的京城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这个厂子专门拍摄科学教育影片,在洗印厂的礼堂内时常会放映一些没有公映的电影。
比如张亿谋的《活着》,邀请作家和圈内人观看的那一场就是在洗印厂放映。
这时候,电影学院还没有大型的放映厅,学生们看电影大多都是去洗印厂的礼堂。
这属于厂子里的内部放映,对电影学院的学生免费,虽然也收票,不过这些票都是赠送的,想要拿到票并不难,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数。
这一晚,贾章柯和同学照例去洗印厂观摩电影,看了两部最新的国产片。
从洗印厂步行返回电影学院的途中,大家都很沉默,这两部片子让他们太失望了。
拍摄手法落后,情节假大空,毫无新意,一点都不真实。
“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你们看看现在的华国电影,都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人说好,都是自己骗自己。”黑暗中,贾章柯略微激动的说道。
“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拍?”有人为难道。
和贾章柯一起的都是文学系的学生,文学系原本叫做编剧系,分为影视剧本创作和电影史论两个专业,贾章柯学的是电影史论。
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国内外的电影理论,属于纸上谈兵。
拍电影都是导演系和摄影系的活,和文学系不沾边,顶多就是写写剧本什么的。
更何况,这几个人在电影圈没有关系,家里也不富裕,甚至吃饭都成问题,怎么拍电影。
想想确实苦闷,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于是,他们买了几瓶啤酒,坐在电影学院宿舍楼的消防楼梯口喝酒聊天,发牢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表达一下愤懑的心情。
喝完酒,摔了酒瓶子,发泄够了,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缓过神来,聚在一起,觉得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他们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这个小组目前只有三个人。
事实上,就是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觉得国产电影不好看,想自己拍电影,喝了酒吹了牛之后面子上挂不住,就弄了个小团体出来。
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想好要拍什么,更没有拍片子的经验。
凭着的只有一腔热情,想要拍出好电影,拍出真实的电影。
在京城电影学院,有抱团儿的说法。
这是指在学校学习期间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的组织成的小团体,一起合作做事。
拍电影需要团队合作,管理系做制片人,导演系的做导演,摄影系的承包摄影和灯光,文学系写剧本让表演系的来演。
所以说,这种抱团的小团体很常见,贾章柯他们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团体可能存在很多年,毕业后大家也一起合作下去。
也可能出现分歧,中途就解散掉了。
实验小组成立后,三人就商量着怎么才能拍电影,总不能说说就完了吧。
“老贾,你不是和导演系的那个红围脖女孩熟么?听说她在圈子里有关系,郑教授很看好她。”小组里的顾争说道,“咱们都没学过怎么拍片子,拉个导演系的过来正合适。”
“这不太好吧,人家不一定能看上咱们。”贾章柯犹豫道。
他有点不好意思,林晓玲是导演系的红人,想要和她抱团组成小团体的肯定不少。
“不问问怎么知道,老贾你是不是怯了?这可不像你啊,一定有问题。”另一名叫做王洪伟的青年开玩笑道。
“别闹了,我问还不成么?”贾章柯无奈道。
贾章柯和林晓玲一直都有联系,上次好梦公司办开业仪式他还过去帮忙了,大家的关系还算不错,他到导演系找林晓玲说了一下。
林晓玲觉得挺有意思,她和贾章柯熟悉,就答应加入了这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整个过程很平常,没有任何的传奇性。
就像是几年前的冬天,林子轩、葛尤和冯晓刚第一次见面,也是喝酒,发牢骚。
那时的他们一个是少儿栏目的播音员,一个是跑龙套的演员,一个是剧组的小美工。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初看着平淡无奇,多年后就会成为传奇。(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九章获奖
《活着》在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葛尤以精湛的表演进入了记者们的视野,有法国记者对葛尤进行了一场采访。
国外的影人对这位来自华国的男演员并不熟悉。
葛尤在电影里塑造的人物表现的苦涩困窘,对生活的变迁带着一种无奈的从容和豁达。
他现实中却给人感觉幽默风趣,戏里戏外存在着不小的反差。
葛尤不像有些演员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遮掩自己的短处,只说光鲜亮丽的一面,他比较实在,记者问什么就说什么,他觉得事无不可对人言。
当然,涉及隐私的地方他不会说,太过敏感的话题他也不会说,他就说自个的事儿。
一些外国记者为了博取话题,会引诱华国的演员说一些针对华国的言论。
葛尤的实在让一旁来自香江的翻译有点愕然,不知道该不该如实翻译。
比如,记者询问了葛尤的演艺经历。
葛尤在进入演艺圈跑龙套之前在公社里负责喂猪,后来考文工团,面试的时候他表演的小品就叫《喂猪》,主考官觉得葛尤表演的很好,有生活气息。
就这样他进入了演艺圈,跑了十年龙套。
这位翻译对葛尤所有了解,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葛尤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华国著名演员,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
这么一说,葛尤的形象在法国记者眼中瞬间就提升了无数档次。
养猪什么的肯定是体验生活,这对于演员来说非常正常。
除了葛尤,国外的电影人对《活着》的原著小说同样产生了兴趣。
在影片放映的时候,片头会出现一行字“根据林子轩小说《活着》改编”,下面还有补充“原载《百花》杂志92年第四期”。
不少外国人看到这句话,就向《活着》的投资商打听小说的出版状况。
在得知《活着》还没有外文版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惊讶,觉得这么优秀的小说应该翻译引介到西方来,让西方读者看到。
张亿谋的电影无形中给《活着》这部小说带来了国际上的关注度。
有位叫做让路易的法国投资商准备到华国和张亿谋讨论新片的筹备事宜,他想在京城见一见《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