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华北、关中地区,恰恰不是土地兼并集中的地区。
宋代发生在江南地区的方腊起义是什么性质?只要查查史料,你就会知道,方腊确实是佃户,他可能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唯一一个佃户,也就是说,他不算自耕农,而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的。可是,方腊起义根本不是佃农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方腊是被宋徽宗的花石纲逼反的,所以方腊起义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斗争,与土地兼并没有关系。
如果仔细去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沿革,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中国的皇权给农民打造了三副手铐。第一副是土地税,第二副是人头税,第三副是徭役。这三副手铐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唐代以前,徭役很重要,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的瓦岗寨起义,都是因为不堪徭役负担才爆发的。农民不仅要交粮交租,还得出人,陈胜、吴广在去戍渔阳的路上失了期,按律当斩,于是他们才揭竿而起,这是农民与皇权的斗争。
到了唐代中期,宰相杨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搞了一次“两税法”之后,基本上废掉了徭役,农民交钱就行,国家雇人去干活,主要把税放在了土地税和户税上,也就是人头税。结果是什么呢?唐代中期以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个基本的特征,都是失地农民因苛捐杂税太重而揭竿而起。所以,它也是老百姓和皇权之间的斗争。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前期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实行之后,完全不收人头税了,只向土地要钱粮、要税赋。于是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全新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因为人口在增长嘛。所以,清代后期遇到的问题,甭管是前期的什么天理教、白莲教,还是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当中的会党,基本上都是失地农民进入江湖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组织对旧的朝廷的皇权结构的挑战。
中国的农民战争,其实没有一次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即使是因为土地兼并,也不是一般地主搞的。比方说在明末,明神宗特别喜欢小儿子福王,就赐给他大量的土地,叫皇庄,此时的土地兼并显然还是出自皇权手中。
那么,中国历史上造成大规模社会动乱、血流成河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呢?看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皇权收钱,真是要钱跟要命似的,从先秦时候就发明了一套特别成熟的制度。比方说保甲制度,就是一定地域内的百姓形成保甲组织,国家只向这个组织的头儿里正要钱,如果收不上来钱,就打里正板子,打死为止。里正不是基层公务员,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上里正之后,反正顶着国家的要求,我就鱼肉乡里,坏人当里正会当得特别爽。另一种就是,里正是一个好人,不敢逼乡亲,那怎么办?自己赔得倾家荡产。这种事在“二十五史”里面屡见不鲜,“中产之下家皆破”,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如果你觉得我这种叙述很枯燥,建议你去看聊斋志异里边促织那一篇,讲的是皇帝喜欢斗蛐蛐,就逼里正,结果把那家人逼得家破人亡。
蒲松龄写促织跟写其他故事有点儿不太一样,饱含感情,这是因为蒲松龄自己就受过这个苦。康熙十三年,山东大灾,蒲松龄家几乎绝收,他差点儿把自己的女儿卖掉,所以他是深知保甲制度对民间的迫害之狠的。
这套制度似乎是中国人的独创,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也有所谓包税人制度,有一点儿中国保甲制度的影子,但是没有中国发展得这么极致。皇权对于民间的敲骨吸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极具创造力的。
前不久我看到一则史料,是在秦晖先生的讲座当中看到的。清代号称“蜀中三大才子”之一的大学问家、戏曲专家李调元,写过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特有意思,说四川有个民俗,谁家买了田,大家都去贺喜;谁家卖田,大家都说是他是败家子而鄙薄他。可是有一天李调元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刚把地卖了,特别高兴。李调元就感到奇怪,你明明就是个败家子,还高兴什么呢?就问他原因。
这个人说:“你不知道,我爷爷在的时候,家里有上千亩的地,可是我父亲只分到200亩,到我手里就剩10亩了。这10亩地好好种,养活自己不算难,可是朝廷的捐税全向我这10亩地要,把国家的征赋交掉,收入的13就没了;地方官还有各种加派,派来派去,且不算劳动力的成本,种地的收入还不够养活这地的呢。没办法,我只好把它卖掉,租别人家的地种,当佃农。反正朝廷朝地主要税,我事先跟地主说好一年的收成分他多少,我苦苦干上一年,好歹还有一点收入。如果我自己拥有土地,直接面对国家,面对公权力,我什么收入都没有,所以我必须这么干。”
李调元一听,这笔算账算得很对,换了我也得这么干,我家也有地,我也卖了行不行?那个人说:“你别犯神经病了,你不能卖,你是当官的,你爹是进士,你也是进士,你还当过朝廷的大官,地方胥吏不敢跟你胡来,你有一层保护伞,所以你不该卖。”李调元一听,说得对,我确实不太受骚扰。
大家知道李调元后来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回家之后,把所有的子孙集中到正堂训话,说:“子孙何可一日不读书也!”意思就是,想好好地活下去吗?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必须读书,中进士,当官,跟皇权搞到一起,获得这张保护符;否则,当普通老百姓你们是活不下去的。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的交易成本就会变高
江浙地区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方腊,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兼并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这个结论下得恐怕有点儿草率。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你不要看大家都在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但是观点也分两个极端,刚才我提到的是其中一派,他们担心土地兼并。还有一派与此相反,他们担心的恰恰是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土地的购买兼并、征收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前几年于建嵘先生抛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书中说2004年前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主题发生了一次切换。2004年之前主要是抗粮抗税,农民不愿意交租子;2004年之后,农业税取消了,农村的社会矛盾主要就变成了征收土地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主题一切换,抗争的整个景观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农民抗粮抗税,对策就是跑,整个抗争相对温和一些;现在为了土地,那就得站在自家的地头进行抗争,所以抗争显性化了。
第54章 现代化的本质(2)()
更重要的是,原来抗粮抗税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穷地方才抗,富地方少有这种情况。可是现在土地问题恰恰多发在富有的地方,经济发达的地方维权抗争得更厉害,所以矛盾显然激化了。更要命的是,原来抗粮抗税只是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现在不一样了,有一帮律师开始下乡(当然律师主流是好的,但是总有一些律师无利不起早)跟农民说,我们帮你打这个官司,打赢官司之后你分我多少多少钱。很多律师一介入农村的土地纠纷,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因此,有一派学者说,现在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承包权,征收土地都这么困难,如果变成了私有产权,拥有了物权法的保护,农民的地还弄得上来吗?
地权的逻辑作者贺雪峰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是我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每年有两个月是住在农村的,带着一个团队在农村搞调研,非常了解中国农村。他说,现在如果农民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农村土地兼并购买的时候,政府连人都找不着;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宁愿把土地撂荒,为什么要卖给政府呢?交易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你觉得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全球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虽然说这几年经济发展得还好,但是基础设施真是一塌糊涂,如果按高速公路的长度来排名的话,它还不如博茨瓦纳和斯里兰卡,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征收不上来。
有一段时间,塔塔集团想在印度征一块地盖个大工厂,就跟农民说,你们把地卖给我,你们到工厂上班多好啊。农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你们端茶倒水?种着地多好!死活就是不卖。所以很多公共建设都很难在印度推行下去。
台湾也是这种情况,陈水扁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就曾经运用铁腕,要拆两块地建大安森林公园,结果闹得鸡飞狗跳。他第二次竞选台北市市长落选,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最典型也最具有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日本。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工。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完工,为什么?也是因为征地。因为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无论给多少钱当地老百姓都不肯把地卖给政府。虽然法院有裁决,但是农民还是坚持抗争,也有很多记者、媒体、公知、学生为他们抗争。最后农民们想出一个绝招,他们在土地当中划了一平方英尺土地设置为共有土地,所有愿意支持他们的人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既然几万人共有这一块土地,拆迁就不单单是个别农民的事了,政府得跟这几万人谈判才行。农民的目的就是让政府干不成这件事。
所以到现在为止,成田机场这么有名的国际大空港,想建一个2500米的跑道都不行。成田机场还发生过一次飞机剐蹭事故,为什么?跑道不够用啊,所以大型客机无法降落。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还一筹莫展。成田机场的征用委员会还曾经发生过一次集体辞职事件,因为实在干不下去了。20世纪70年代还发生过一个悲剧,这个征用委员会的委员长被人毒打,最后不堪羞辱,举枪自尽了。
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们的基础设施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迅速地发展吗?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样说,现在搞的“土地流转”也是一种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做法,这和土地私有化是有本质不同的。
没有产权和自由交易,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有些经济学家就给这个担心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牵扯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科斯这个人了不起,他作为大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世界的全新角度。他靠两篇文章成名,公司的性质和社会资本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观点——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想要市场的效率高,交易成本就得低;交易成本一高,整个制度环境就会发生变化,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因此就说,科斯老人家说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高,所以是不划算的。
这个道理讲得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只见小道理,没看到大道理。如果一味降低交易成本,那交易成本怎么才能更低呢?直接把农民变成奴隶,让他们白干活儿,只给碗饭吃,只保持肉体的自然再生产,交易成本不是更低吗?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那都是国家免费使用农户的劳动力。可是我们要这种发展效率吗?有时候账不能这么算。
慈禧太后贪污600万两海军军费建了颐和园,可是颐和园现在每年的门票收入有三到五个亿,当年的600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也就30亿,等同于每年有10%的收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理财产品了。那能说慈禧太后干这事儿是对的吗?账不能这么算。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先生是研究经济史的,他曾得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结论:在美国黑奴时代,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经济的效率其实比北方工业经济的效率还要高。福格尔只说到这儿为止,但是往下一推论,就是说,美国经济想要发展,干脆把一部分人再变成奴隶吧,这对国家是好事。
可是,经济学家能这么看问题吗?所谓的经济学家是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人类内心的良知呢?我们所有的道德呢?如果我们要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又不给他产权,从而换取效率的话,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极端结论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奴隶制,效率就会更高。可是能这么做吗?
人类进步不光包括经济进步,还有道德、良知各个方面的考量,我们凭什么认为,为了农民的利益考虑,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决断呢?如果哪个经济学家这样想,我觉得他就背离了20世纪经济学的基本成果。我也建议那些经济学家再去仔细读一读科斯先生的原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没法跟他对证,但是他的原意是,任何交易成本成立的前提都是交易者拥有完整的产权和自由交易的市场条件。如果脱离了这两个前提,没有产权、没有自由交易,那还有什么交易成本?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在此,我们引用一下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哈耶克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他也是引自富兰克林的。他说:“当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而获取所谓的一点点保障的话,那他既不配拥有自由,也不配拥有保障。”今天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公权力以为剥夺公民一点点自由就可以给他们保障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民既没有了自由,也没有足够的保障。
贫民窟不是城市的牛皮癣
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还有一个很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防止城市出现大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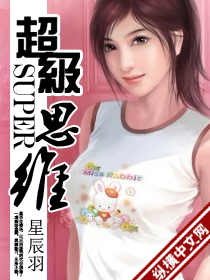



![[猎人]思维不受控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33/33002.jpg)


![[猎人]思维不受控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87/8754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