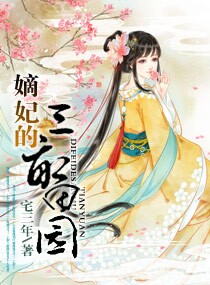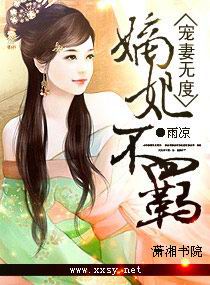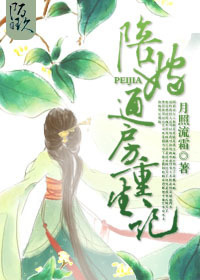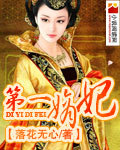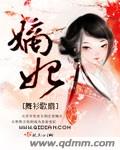陪嫁嫡妃-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离他近,遂低了声音道:“王爷,这人不拿下怕是有很大的隐患,但若这个时间拿下也不大妥当,需寻了合理的时机一次就办到位。”
他眼神带了笑意玩笑道:“王妃,他可是你太子哥哥那边的人,你不怕你太子哥哥日后知道是你给我出的主意,找你秋后算账么?”
她冷下脸但即刻换了平和:“王爷,他日太子寻了我的错处,我自有应对,王爷无须考虑这些,只管按律执法。”
他见她变了脸色,一时也觉得自己太过唐突,陪了小心道:“曦儿,和你玩笑罢了,朝廷命妇若都是你这样明大义的贤内助,何愁国不兴旺。”
她淡然笑笑,也不揪着他不放,和他说正事:“王爷,近来夏州的粮食买卖有些异常,怕是西夏那边粮草有些短缺,我朝封锁了和夏州的贸易往来,但和西夏交好的匈奴和金国贸易还在正常进行,西夏的李元台娶的妃子中就有一位是匈奴公主。太祖时期也曾将宗室女梁琼文下嫁给匈奴乌图单于,虽抬了公主的分位但未有已出,再则乌图单于病故后,其子呼兰收了梁琼文在后宫,呼兰后宫佳丽无数,年长的梁琼文并无特别恩宠,只因大宣公主身份,面上礼遇而已。但李元台不同,他有极强的政治野心,虽匈奴公主并不是元妃皇后,但他一直很是恩宠,这回屡犯边境,怕也和匈奴有了私下结盟,我朝断了西夏的粮食,我担心他们通过匈奴人买我朝的粮食,暗地里支援他们。”
他沉吟道:“曦儿,你所想极为周到,不管匈奴是否和西夏结了同盟,我们都要防备着才好。”
正说话间,双花率了众仆妇张罗好膳食。张全对他点点头,他遂扶了她去用膳,虽这里不是靖王府,但厨役里张全安排了两个得力的太监把管着。
饭间一众人等侍候,他虽带了笑意,也给她奉菜,但并无亲昵言行,她习以为常地平静用饭。
膳后他未久留,去了军中,她亦是极忙的,带了慈姑思同把这府邸全都细细了解一番。毕竟在边疆,尽管段夫人已经准备得很是尽心,但要是宴请六桌的内眷,也还差了许多用品,也无有这样大的厅堂,末了只得因地制宜,厅堂摆了四席,东厢房摆两桌。
她这边安排着,余春泉带了七八人送了明日要用的杯盏碗碟并一应食材,这些人都极为规矩小心行事,当夜留了三人熬汤,做着明日的菜式准备,她遣了思同安置这些人。
梁靖恒从府里往军里的路上,心里也在反复思量。大军的先头部队会同原州灵州人马呈三路夹击野利的骑兵,以往我军对付骑兵常处于弱势,这回采用了狄云新战术,让西夏骑兵死伤不少。
骑兵速度快,打运动战,闪电战极占优势。这次狄云用少量的骑兵正面出击做掩护,步兵从左路攻击到野利的重骑兵的内里,用大刀砍马腿,长斧砍骑兵,让西夏重骑兵阵法大乱,想后退转弯但集结的队形又不如步兵的灵活,一时踩踏无数。重骑兵铠甲笨重,落马后起身逃跑极为不便,一旦落地几乎无还手之力,死在大刀下无数,让西夏的王牌骑兵受到不小的重创。
至此李云台修书想议和,军中不少将领也主张议和,议和也不是不可,毕竟征战极大消耗国库,也让边疆百姓流离失所。但议和是有前提的,首先李云台必须称臣按以往的岁贡纳贡,其次确保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畅通,再一个承诺永不在边境进犯。
这三条对于翅膀长硬的李云台来说,绝不会接受。即便李云台同意这些条款,但此人极为奸诈,怕是以时间缓空间,等骑兵先撤回修整,再图谋生变。
军里各主将汇集一堂,议和与主战的众说纷纭,双方讨论的十分激烈,议和有议和的理由,主战有主战的主张,都督王中基只是喝着茶汤并不发话。
往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主帅先稳住目前的局面,然后飞马快报朝廷,让圣上定夺。
纵观前朝的历史,武将虽在沙场浴血奋战,但朝中基本是文臣当道,文臣没有亲身到过边关,无法想象边关的实际情况,加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考虑,很大程度上影响皇上的判断。若是皇上身边有那么几个私欲重的奸臣当道,不仅掣肘前线的主将,更有甚者公报私仇,不时地在皇上面前进谗言,最终做些个祸国殃民之举,不但生灵涂炭,严重时发生朝代的更迭。
说起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真正又有几个将士敢吃熊心豹子胆,自行决断?除非是极得皇上的信任,皇上授予了极高的权限,否则不定哪天就会秋后算账。
本朝王元帅一系倒是在朝廷一言九鼎,说话十分地有分量,直接影响到咸帝的决策,但这会子都督并不表态,无疑是让他自己拿主意。
他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一个不慎就会影响大军的生死存亡,他虽饱读兵书,但毕竟没有亲临战场,没有任何一丝半点的经验。
他起先只是聆听各将领的言论,不停思量是战还是和?
反复地考虑,反复地想着利弊,末了,他叫停双方的争执,不再讨论是战还是和,改变争论的矛头,闲话李元台。
原本李元台并非西夏王位的继承人,应由他的侄儿李克思续位。当年太宗在世时,李氏地方政权历经三百年的发展,逐步发展到傲视群雄的部落,在西北众小的番邦里有很大的威望,太宗灭了内地小方镇割据势力,当时也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消灭这些番邦。正当太宗准备出兵时,李元台的族兄李继光因和父亲产生矛盾,率了族人到汴梁称臣,这其中就有年仅十二岁的李元台,李继光不仅愿意留在京城,还向太宗进献了四州八县。
太宗在当时的局面下多方面考虑做出了安抚的抉择,其中缘由一个是怕激化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一个是因大宣没有骑兵,如果完全使用武力不能十拿九稳必胜反倒被动,再一个如果攻打西夏,也出师无名。
在此背景下,太宗重赏了李继光及族人,并授予银州节度使,在大宣的支持下,李继光继承了西夏王。在此阶段,李继光基本还是维系了大宣和西北番邦的和平,在大宣和契丹的战争中,西夏没有联合契丹对大宣发兵,同时维护了丝绸之路的正常通道。当然作为西夏来说,也有自身的考虑,若是契丹一旦打进中原,那么契丹势必就会强大起来,西夏也将岌岌可危。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系到李元台掌控西夏的政权,李元台为了夺权篡位,先是带着重金到契丹,愿意归顺契丹,得到了契丹的鼎力支持。随后娶了西夏大将军的女儿为元妃,之后又迎娶了匈奴公主及小番邦的郡主,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处心积虑的多年谋划,一个隆冬的夜晚李继光暴病而亡,李元台在各小番邦的推举下,取代了年幼的李克思,做了西夏王。
李元台取得政权后,也是数次上书愿意和大宣修好,但其背地里却勾结着契丹左右逢源,伺机扩大着势力,逐步占领了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批肥沃的草场和部分良田。
梁靖恒把话题引到李元台的性格及取得西夏王的由来上,让众将分析李元台此次求和的动机及可信性。
一个在左右逢源中成长的人,一个心机莫测的人,一个曾经背信弃义过的人,这样的人能相信么?
养虎为患就已极为危险,更何况这个虎不是幼仔,而是有着丰富政治阅历老奸巨猾的狐狸。
梁靖恒在主和的呼声渐弱之时,斩钉截铁地道出自己的抉择:主战不主和,全面向西夏开战。
第93章 破釜沉舟的打算()
王中基只是听着,自始至终不发表自己明确的观点,梁靖恒定了战略方向,转身望向王中基道:“王都督,你认为是战还是和?
见梁靖恒开门见山问策略,王中基指头轻敲着盖碗的盖子,环视着屋里各将领,这些将领基本都是帅府选得人,对帅府有异心的要么被排挤,要么压制,今日能在这议事堂的人,绝大部分是帅府的嫡系,只要他反对梁靖恒,梁靖恒就调遣不了这将士。
他叩着茶碗缓缓道:“王爷,此前我虽在这夏州坐镇,源于我长期镇守边关,如今皇上派你率三十万大军西征,国之大事应由王爷定夺的好。”
方才晚间用膳肖芷曦委婉地告知了王中基的态度,这一刻王中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梁靖恒心里也明白了大概。
已近子时,再议不仅疲惫,也没有一个充裕的准备,他散会之前,温和但态度极为坚决对各将领申明:这次开战只能打绝不能和,战略方向已定,军中任何将领切不可还有着和的想法,不论是做破釜沉舟的打算也好,还是做背水一战准备也好,只能往前绝不能退后,若谁还有着和的想法,还试图想和西夏和谈,不论是谁,立斩无赦。
众将见他当着都督的面说出这样强硬的话,顿时一凛,一时之间各种神情都有。
他对众人神色视若不见,宣今日就议到这里,明天接着议,所议也只一件事,攻打西夏的具体战术。
在众人的琢磨中,他向王中基招呼后,回了临时府邸。
一众人等见他离去,纷纷问王中基主意,王中基深思道:“各位将军长年征战在外,对朝堂之事不一定事事都清楚,但靖王爷斩了皇上庶出哥哥恭亲王,瓦解恭亲王和契丹的勾结,大家想必知晓一二吧。靖王爷虽看着清雅,但他手段是狠厉的,你们自个回营仔细想想怎么征战西夏,明个我给各位提个醒,切切不可说和谈,我琢磨着明天靖王爷会拿一个有头脸的人杀一儆百。”
王中基的一席话,众人心里重新衡量着梁靖恒,又见王中基方才对梁靖恒的战略并无反对,主战的到也没有说些什么,主和的有几个发着牢骚:“都督,虽说这靖王有调兵的兵符,但此等大事也应奏于圣上,由圣上定夺才好,靖王连圣上都不奏报,自个就决断,若是战败,大宣的脸面何在?那李元台要是借此由头打进中原,三朝的太平就会毁于一旦,到那时怕是悔不当初。”
王中基征战沙场几十载,历练下来极其沉厚持重。方才他虽淡淡地听着,看似不经心,但议事堂里每一个人的言论他都极其认真地听了去,暗地里也在琢磨是战还是和?
如果这回没有梁靖恒,他坐镇西北也要决断,奏报皇上必定是要飞马快报的,但帅府也会听他的一个基本意见,在此基础上,帅府在朝廷拿出自己的观点,这观点对咸帝的旨意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国库的储备渐渐丰盈,不比建朝初期百废待兴,征战西夏还是有底子的。再则如今西夏越来越猖獗,若是不狠狠打击一下,怕是对西北一带更是骚扰不断,长此以往,势必引起匈奴,金,辽以为大宣朝中无人,各个都在边境挑起争端,到那时恐怕更难对付。
到不如下定决心把西夏打下来,把旁的番地想一哄而上趁乱打劫的想法控制在萌芽状态,让他们以西夏为戒。
入冬西北比中原气候冷上许多,他回了府邸,见西厢房的火烛还燃烧着,知她还未休息。他凝视着朦胧的剪影,深深呼吸几口清冷的空气,眼神深处弥漫着柔软。
她定是在等他的,这回到夏州,她对他极是体贴,虽说在靖王府她也循了例,等他回府才安歇,但和在夏州等他回府完全不一样。
在靖王府她只是守着规矩,对他是隔离的距离,虽挑不出一丝半点的错,但她的心却是冷淡的。
但此次从汴梁出发以来,她渐渐对他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体贴。他也知她是为了稳定军心,让他心情保持平和,不让他为内宅之事分散精力,好一门心思攻敌。
无疑她极其识大体,在国事和家事面前,她能放下自我,把大宣国之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她的心胸怕是无数男儿都望尘莫及。
若是当今的皇后有她这般远识和豁达,有她这般心系天下,怕是父皇不会对皇后娘娘这般防备,更不会时时临幸嫔妃宫人,让皇后娘娘暗暗心生哀怨。
外面侍候的太监见他回府,赶紧迎了上去,她在屋里听到动静,让连翘挑了厚实的帘子走出来,他立马解了披风裹在她身上,送她回屋责备道:“曦儿,外头冷,又大半夜的,就这么的出来,也不怕着凉。”
她浅笑着道:“就这么一会,哪里就会着凉。”
他满脸的不高兴:“你也别逞能,你本来身子就有病,别看这一会,要是胸口吹了冷风,到时病了躺这里可没人照顾,我后天就要开拔了。”
慈姑吩咐厨房上宵夜,张全又赶紧地打热水,她褪了披风问:“王爷,后天大军就开拔么,我是随了王爷,还是在夏州?”
他上前握她的手,见手心还热乎,长出一口气道:“曦儿,你就在夏州,这回我和你舅舅一起开拔,夏州会留两万的兵力守城,我军是往西夏打,李元台抽不出身攻夏州,你就留在城里,等我打下了西夏来接你回朝。”
自大前天到夏州,大军已休整了两天,差不多也适应这气候,后天出发,体能也跟得上。
她给他盛了猪羊庵生面,轻言细语让他宽心:“王爷,你尽管去,不要挂念我,打仗刀枪无眼水火无情的,你自个要当心,铠甲虽然穿着笨重,但是能防身,不能马虎了,要不把张全和慈姑带上,他两人心细,也好照顾你。”
他接了面碗:“曦儿,我跟前侍候的人多,你无须多虑,你把自个照顾好就阿弥陀佛了。”
她坐他身旁,给他碗里夹着笋丝,他挑了一筷子面递到她唇边,她立刻飞红了脸,垂头吃了下去,随即起身掩饰地让张全给他收拾行李。
他坐在桌边,好笑地看着她的不自在。这女人偏偏和旁的人不一样,旁的女人常常在夫君跟前撒个娇,说些个讨喜的话,她非但没有一丝的娇媚,反倒避了开去。
他笑着吃了大半碗面,关照她早点休息,起身回房。她期期艾艾地送他,他温和让她留步,她一时地有些歉意,看着剪平了的手指甲。
慈姑给她铺着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