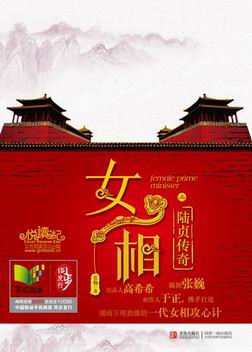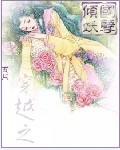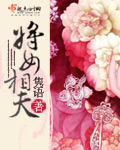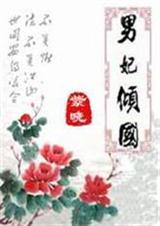倾国女相:陛下,请矜持-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时华盈琅嘱托过,若是提出的交换要求里包括华氏钱庄的西蜀银票独立兑换权,直接拿他们西蜀的圣旨压人就是了。除了这个坚决不能松口之外,没什么是不好商量的。
而安玲珑真的面见了夏侯少主的下属之后才觉得,幸好只有这一条是坚决不能松口的。
华家在西蜀的产业经营权,华家在三国其他地域的产业所售卖的东西
甚至是在南越那个已经成为传奇的“商世”大市街,都被直接讹诈掉一块大好的宝贵地段做了夏侯家的商铺。
第185章 务求兴天下之利()
安玲珑的幸不辱命,也只是面上这样说而已。
安玲珑回来之后为此懊恼后悔不已。
华盈琅笑着安慰她:“你可能不知道,你付出的越多,局势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要相信,仰人鼻息的日子并不会很久。而夏侯渊,虽然心思深沉,却并不是一个奸诈的阴险人物。”
“他这是也看到了我的目的,想和华家结个善缘的。”
这话说得安玲珑一阵恍惚。
她十分怀疑,自家的小姐自从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开始昼夜不停地埋首卷中之后,她的智商就越来越让人慨叹了。
为什么现在小姐说的话她都有的听不懂了呢?
难道说她读的书真的太少了?
其实不然。
华盈琅在回归恭州的这短短十几日里,每日坚持着逼迫自己白天出门走访来去,各行各业的人都打了交道,来锻炼那原本十分得罪人的一张嘴;
晚上回来,几乎是立刻就选择挑灯夜读,来填满自己已经临近枯竭的智识。
毕竟,她终究不是本地人,很多时候,她的想法都让人很难理解,也根本不符合实际。
再加上华家之大,身为家主,有时还会处理些账务
每每弄到子时都不带停歇。
好在是这个身体原来的主人当真是才女——绝大多数的典籍她只消读一遍书,藏在脑海深处的那些记忆就一点点浮现上来,还带着这原来主人的想法和感慨,一时竟有时空错乱、灵魂相交的感受。
这时候华盈琅才渐渐的明白,她到底是附身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而原来的华盈琅大小姐,又是怎样的才动京华,名冠天下,惊才绝艳,宛如谪仙。
一点点的将自己还原成那个不同于自己的人,有灵魂,有思想,有情感
这也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坚持建好华氏的家庙的原因——换成在过去的任何时候,她都会直接认定这是干脆的迷信行为。
但现在她明白了。
今人以为世界上没有神灵鬼魂,难道古人就感觉不到,靠祭拜那些神灵,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吗?
没道理我们的祖先,会真的那般傻。但是他们知道,敬畏一些什么,总是比什么都不怕,一心无所畏惧好得多。
无所畏惧的人往往是为所欲为,在心底敬畏道义的人,方能约束自己的所为。
不过是一种敬畏,一种传承罢了。
人,总是要有一个信仰的。
最朴素的道义信仰,就体现在这种对于真正的英雄先贤的崇敬和颂赞当中。
所以她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小事——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买一块地建几所草房子,让商人有地方经商贸易;将华家的家庙建起来,允许外人也来参观拜祭华家的家庙,或者是在家庙当中摆上先贤的牌位供人瞻仰祭祀,这都是小事。
往小里说,不过是助人的义举,或者是对自家购买的地方的一个规划;
再大一点,也最多是华氏一个家族的家族内事务,没有人会去干涉一个人家的家庙构建成什么样子,建的好了祖宗荫蔽,建的不好也是个人家族的风水问题。
第186章 三国相争西疆殇()
但是华家不一样。
华家具有自己的领袖的影响力。这些再说,也不过是琅琊华氏嫡系自己搞出来的小事情,但是对天下人的引导却是远远不止的。
这样的小事做好了,会让人看到诚心,以及华家一举一动当中带出来的,百年大族,世家风范。
民心所向,效仿之,则天下行至。
华盈琅的变化,华家人都看在眼里。
他们庆幸,小妹三姐终于回来了。
他们也感慨,一个人成长的不易。
华氏如今的一切,大概再也不能离开华盈琅。
相对于木炭从夏侯氏“进口”的艰难,华盈琅并不担心。
她知道,一味依靠外来的商品和物料,是农业社会的大忌。
本来,农业社会一般都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点的。如今像木炭、木料,以及由木炭产出的接下来的炼制铁和铜,都必须依靠外来的输入才能存活,这本来就是不应当的事情。
更何况,现在出问题的,是历代的统治者对西疆这片地方的明贵实贱,面扬心贬。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样的情形,来说西疆也是不为过的。
天下三分,各国之主都在尽力争取到这一片富饶的地方。六百年之后的今天,这里已经不仅仅只是产粮大户,更应当说是各国力量的象征。
能够争取到西疆划入自己国家的领土,这就是三国统治者的一项丰功伟绩了,算是开疆拓土,文成武就;至于说怎么治理好它?这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反正不知多少年后,也许就只要几十年,这里就会再度易主。
到时候治理得强盛繁荣,难道不应该说这是在将自己的心血拱手让人?
而他们所做的,只要保证西疆这片土地是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夺得的,而不至于在自己退位或是驾崩之前又丢掉,那就可以了。
所以西疆的地位,往好听里说是丰饶的兵家必争之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频繁易主的事实,西疆干脆可以当成是三国之间争夺不休的“殖民地”。
能掠夺多少资源就掠夺多少资源,让西疆这块地方给出最大的产出,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西疆之于历代统治者的终极存在意义。
全境树木殆灭,难道还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吗?
让西疆这片荆楚之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恢复植被覆盖,想要靠植树,现在看来还是太悬了。
但是华盈琅知道,六百年过去,西疆的土地已经在这样的争夺之下,逐渐出了问题。
一次冷兵器的战争对一个地方的生态影响并非不可恢复,但是长达六百年的掠夺,已经让这里不堪重负。树木殆尽,水土焉附?
西疆在三国的联合压榨下,正在竭尽全力的供养天下人;而这些天下人当中,并不包括西疆自己人。
一方水土养天下人去了,一方人怎么办呢?
华盈琅想起一种植物。
呐,这就要等到春天了。
不过现在试一试,那还是不打紧的。
第187章 烈火焚烧若等闲()
——那真是一个万物复苏生长的好时节呢。
华盈琅从南边的山区买了一大批的裹着泥团的竹鞭。
竹子,尤其是毛竹,长得那么快又能长到那么大
多好的建筑材料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大格局的代替木材有没有?
当然,那些重要的木材肯定是不可能代替的,但那属于一地的特产——一地特产,没道理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竹子长起来了,还可以烧竹炭呢。
她是知道的,做了那么久的特战队员会连竹炭都不知道?
那是常年寄居在她的口鼻上的物料呢,尤其是过火场和原始森林的时候。
竹炭不好烧,主要是因为竹炭烧制所需要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正常看来,竹炭烧制时要想让产物少烟,那就要不停的变化适合的温度,这和传统闷烧木炭直接将木料塞进窑里就可以的做法差异很大。
技术是一项重要的东西。
华盈琅相信,在这样木炭吃紧的情况下,如果让西疆百姓自己摸索,不超过几十年,劳动人民一定也能自行摸索出生产竹炭的方式。而她对这项技术的了解,也仅仅是局限于大致而已。
但是她相信,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点,足够让人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智慧产物,因为灵感的一时爆发而提前问世——越是技术****性强的东西,越是这样。
很快,华家的第一批瓷窑里,就多塞了些东西进去。
粗大的竹子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竹节,分着放进瓷器窑里。窑子开了火。
相比烧炭,瓷器烧制的技术和工艺进步就快多了,因为皇室贵族们的要求是永不能被满足的。
这是之前华盈琅对瓷器师傅说,这样兴许能让竹节蒸腾出的翠色均匀的附着在釉上,较之原来的瓷器就更加让人喜欢,不像仅仅用颜料那样涂在上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自然。
然而实际上,看到从缝隙中升腾出的烟雾和窑底不时透出明亮白光的入风口,她正在心底默默的忏悔。
——早知道,不如让他们每天烧过瓷器之后再加竹子继续烧一会好了。
烧制瓷器的高温足够竹子炭化,但是她实在是不能想象,如果竹炭烧出来了,原本的“主产品”瓷器,会被污染成什么乌起码黑的样子
是她错了
愧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就像烧瓷的师傅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三彩流彩瓶会流出什么样的釉色。
傍晚时分,窑内渐渐的冷却下来。瓷器即将出窑。
而让烧瓷师傅十分不解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家主似乎比他还激动的样子。
瓷器端出来的一瞬间,尽管那些放在边上同样受到炙烤的竹子还没有拿出来,华盈琅却已经隐隐在心底疯狂欢呼了。
竹炭,一定是成了。
不过更大的惊喜尚且不在于此。
——这一批烧的是三彩瓶和白瓶,和竹子同窑的是白瓶。
这一回的白瓶,烧出来似乎与之前真的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程度还是出乎人的意料。
第188章 白沙在涅玄映雪()
这样的白瓶,按理应当属于白瓷,特点就是晶莹剔透,所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芭斋也可怜”。
但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这一回给瓷器加上了颜色。
瓷器烧制之前表面的釉是粘稠的透明半流体,烧制后便凝固下来。
从造坯到烧结再到素坯吹釉上釉,瓷器烧制这一整套的工艺流程,无一例外都是十分精细的活计。
烧瓷师傅自然不会让这个单单是素胚上釉就耗费他许多心血;持续了十多天窑烧不眠不休轮班倒看的试验,心血白费,付诸东流。
烧瓷师傅十分小心的用水洗去表面的碳灰,表露出来的白瓷上有了一层淡淡的烟雾。
这一层烟雾就是飘然的竹炭细颗粒在瓷器上留下的痕迹,由于釉凝固的时间也有差异,这烟的浓淡深浅也各自不同,宛如在水中滴下墨滴后散晕开来,只是这一回便成了凝固的艺术,足以让人永远的惊叹欣赏它的美丽。
华盈琅看着如获至宝的烧瓷师傅——可以想见,这种误打误撞的产物会是何等的吸引文人墨客!
但这并不是主产物,而且烟染的效果也各自不同。有的瓶身就被熏染的黑漆漆的倒是符合原来的预料了。
只是华盈琅仍然不能确认,窑里的那些竹子,到底被熏炙到了什么程度。
打开了窑口和窑顶以通风散热,同时将炭表面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氧化形成白灰附着在上面,也许就可以像白木炭一样,不生灰不生烟气了。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瓷场的师傅们都渐渐集中过来,也不说话。有的就在附近蹲下来,有的三三两两搭着布巾站在一旁——
这些劳动者,冬日里是最不怕冷的了。
过了一会儿,窑顶的烟渐渐散干净了,华盈琅请师傅慢慢的将窑打开,端出里面的竹子来。
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什么“竹子的翠色可以浸润瓷釉”,全都是托词。
但是托词也有托词的好处。
这时候不远处一个一身上下焦黑色,一双手似是烧过的炭火,脸上的皱褶似是风化已久的树皮一样,枯朽而毫无生机的老人,踽踽着过来了。
有人扶着他。是家主三小姐身边的大侍女,黎潇湘。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九华”这个名字。这一段时间,家主经常在华家的产业走来走去,身边陪的就是这个侍女和另一个姑娘。据说一个叫九华,一个叫余容。
都是天仙一样的人物儿,也有天仙一样的名字。
如今,九华仙子却是扶了一块乌黑蜷缩的焦炭过来。
这样强烈的对比——一白一黑,一美一丑,一年轻一年老,一清秀挺拔一枯萎败索,就直直的摆在人的面前,冲击感不可谓不强。
极致的白与极致的黑,如同琼花开在玄武岩上,如同皴黑泥裂的滩涂上嵌入一颗白色的珍珠。
霎时间,光华惊人。
为何华氏的瓷场会请这样一位佝偻逡巡的老者进来?
众人不知其意。
华盈琅看着仍然盖着沙土的竹子,一点一点的用手拨开。
黑炭老者也战战巍巍扶着什么,踉踉跄跄十分艰难的走过来了。
第189章 要留灯火向人间()
华盈琅停下手中的活儿,慢慢站起身,扶着老人的双臂,和黎潇湘一同搀着他坐在旁边已经设好的胡床上。
原来,窑旁唯一的一张坐具胡床,竟然不是给家主小姐坐的吗?
她再一次俯下身,繁丽的衣饰和宽大逶迤的袍袖让她无法蹲下身去。只是弯着腰,一点一点不辞辛烦地翻动着表面的沙子。
竹炭还是要除去各种油腻的分泌物一样的,高温烤出来的焦油,才能变得干净的。
温度降低也不能太快了,一旦与空气接触的面积太大了而内部还有火星,一下子就烧起来,那就得不偿失了。
她没忘了竹子和木头是不一样的,竹子中空呢。
慢慢的手拂弄着这些灼烫过的沙粒,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