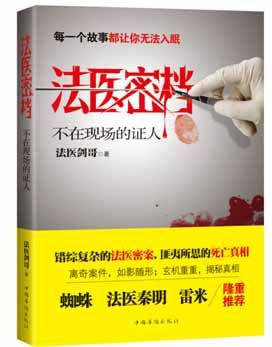乡野法医禁忌-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环肩,说我的话比家的文字还抽象,并且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都暴露了怎么还有生机?
“表象亦是假象。”
回局里的时候是下午,小冷又开始新一轮课程。
我把现场的情况简单和她讲了一下后,将死者遗体暂时放入“大抽屉”里。玲珑像是打不死的小强,刚回到法医室就立刻恢复了精神头,高跟鞋尖毫不客气地落在我脚面上,钻心的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只能强忍着。
“疼吗?”
“舒服极了。”
她脚下一用力,简直要命。
“这回呢?”
“被你这样踩着,太幸福了。”
她抓着我的领口,警告,“这就是对你出言不逊的教训,若日后你胆敢再有轻薄之意,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仙仙欲死?”
啪
又是一个耳光落在我脸上,声音响亮,引来无数学员观望。
玲珑掰这小手,迷人一笑,“他嘴抽筋了,我在帮他。”
可能是嫌我们太不注意形象影响到她上课,所以小冷一气之下了上帘子了。
“就怪你,小冷姐生气了。”
我一个华丽转身,将玲珑压倒在大理石台面上,“她不是经常这样吗,不管她,这回没人能打扰到我们了,来吧,宝贝。”
哗啦
帘子重新被小冷拉开,一双眼睛杀气腾腾的,厉声厉色,“你们两个,出去!”
尴尬地出了法医室,玲珑“始乱终弃”地把我推开,骂我是个瘾君子,随后转身离开。
夜里。
回到公寓的时候不见阮红,但饭菜已经做好。每天都能吃到一个女人亲手为我做的饭菜,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分手后又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即使现在我们以朋友相称,但感觉还是有些别扭。
所以。
我还是应该想个办法,让阮红知难而退才行。
阮红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空饭盒,想必又去救济那些流浪的孤寡老人了。
我叫了她一声,“阮红。”
“嗯?”
我犹犹豫豫,十分忐忑,“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在一起相处过那么长一段时间,说话的习惯和方式大家都心知肚明,阮红一眼就看穿我心里的小九九,从包里掏出一小沓钞票,似乎是用这个办法来堵我的嘴,“我打听过了,县里的房子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我一个月给你一千,这是三个月的钱你收好。”
三个月?她要在这住三个月?
我连忙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房子是局里分给我的,我一分钱都没花怎么好意思往回收钱呢?
“亲兄弟还明算账,以后你就当我是个租客,钱我可给你了,三个月内这里也是我的家。”
说完,她心安理得地回了房间。
这就是阮红的高明之处,掐准时机狠狠将我一军,让我毫无反击的能力,之后再想“请”她走都怕是难如登天。
12,秘密()
深夜。
城市的喧嚣逐渐平息,大地沉眠,只有我在微亮的灯光中独守寂夜。
手中拿着一份被翻过无数遍,已变得褶皱的案件资料,孜孜不倦地一遍一遍翻阅。不知何时,阮红已悄无声息地在我旁边坐下,顺着我的目光静静望着那份资料,说她对“鲛人案”也有所耳闻,对案件的细微之处有一些见解。
差点忘记阮红也是一名刑警,阅案无数,曾凭一己之力破获许多疑难杂案。
我点头,很郑重地向她讨教,愿意听听她的想法。
阮红从我手中接去资料,在柔弱的灯光中翻看几眼。半刻钟后她问我,没有见过鲛人,又怎么肯定就是鲛人作案?我纠正他,之前就已经做过鉴定,所谓鲛人不过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病。阮红摇头,也纠正我,她说的就是这个病人,为什么他就一定是凶手?
为什么?
阮红对案情可能不甚了解,所以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我说,至少在两个现场中发现鳞片,还有凶手留下的脚印,这些都可以证明他的确在现场出现过。阮红再一次纠正我,单凭现场中的某些证据就盲目下判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所有的现场都是可以伪造出来的,如果是有人故意在现场留下脚印和鳞片呢?
“你意思是?”
阮红提醒我,“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巧,鳞会遗落在现场?”
“有目击者的,他们看见这东西了。”
阮红从厨房里拎出一袋东西,又走进洗手间里折腾了半天,出来以后半边脸上都是鱼鳞,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鲛人出现了。
“如果我现在出去你说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是鲛人?所以我才问你怎么肯定他一定是凶手。”
我豁然开朗。
难道有人伪装成鲛人作案?
不能否认阮红说的很有道理,但在没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这只能做为一种假设。
“谁说我没有证据。”
我挺直身子,越发不可思议,“你有证据?”
她睫毛在微光中轻轻抖动着,眨巴了两下眼后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你那么聪明,早怀疑我了吧?”
我问,“怀疑你什么?”
“其实给流浪的奶奶送些吃的是个障眼法。”
“哦?”
她话题越扯越远,“我是给一个人送去的。”
“谁?”
“一会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五分钟后我和阮红离开了公寓,走在寂寥的街头。午夜的光洒落在街面,陆离诡诞。步行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止步在一处废弃的老建筑前,越过面前的层层障碍,阮红在前,我在后,走进了这间阴森森的,连门窗都没有的黑屋子里。
借着窗上溅落的月光,我看见地上满满一盆血,旁边都是血淋淋的绷带。
目光上拉,在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正警惕地注视着我,较小的身子一个劲地发着抖。当我看到她半张脸上黑乎乎的鳞片时,吓得踉跄倒退,踩翻了铜盆,里面的鲜血哗一下流的到处都是。
我惊慌失措,问阮红,这是怎么一回事?
阮红似乎更在意那个女孩的情绪,率先跑过去安抚起她来,“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帮你的。”
我指着那女孩,脱口而出,“她不会就是那个鲛人吧?”
“什么鲛人?她是个正常人。”
我脑子里有一百个问号,在这诡谲荒诞的谬夜里无限发酵,膨胀,却不知道该从何问起。过了一会,阮红拧开旁边的一瓶药,亲自喂“鲛人”吃下,并怜爱地抚摸着她的头,轻声责怪,“姐姐不是告诉过你吗,一定要按时吃药,这样你才会好起来。”
这段时间阮红频繁出门,说什么给流浪者送吃的,实际上就是来照顾“鲛人”的。
“到底怎么一回事?”
阮红目视我,说,“你也看到了,她多么需要人保护,又怎么会伤害人?”
“太难以置信了,我都不知道该问你什么好了。”
“嘘!”
她示意我不要出声,手一上一下轻轻拍打女孩的肩,直到把她哄睡了以后,轻手轻脚回到我身旁。
“到外面说。”
我跟随阮红走到外面,迎着夜里少许寒冷的风,目视着绕月盘旋的黑云。
良久,阮红道破来龙去脉。
那天她赌气从公寓离开,经人介绍去了县里的姻缘庙,可惜迷了路,也不知道走到哪,还一脚踩空,险些从山上掉下去,如果不是这个小姑娘及时出现,她可能就真的没机会站在这里跟我讲话了。
我难以置信,问,“她救的你?”
“我自己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那时我就听说过鲛人的案子,看到她的时候还吓的要命。但她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相信她也不会伤害别人。她真的挺可怜的,这么大的世界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这里虽然四处漏风,还很脏,但至少很安全。”
“不行。”
我还是觉得这种做法过于盲目,不够稳妥,就准备打电话给陈思,让他带人过来把“鲛人”抓回去。可电话刚出来就被阮红抢走,她义愤填膺,如果我今天把叫人把女孩抓走,那就等于把她往死路上推。
“就凭她救了你,你就说她不是凶手?”
“她都病成这样了怎么杀人?再说她才十几岁而已,而且这些天她一直都在这里。”
我一下想起今天上午处理过的那起案子,便问阮红,昨天夜里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她也在这里吗?
阮红摇头,“不在。”
“没有不在场时间,你怎么证明她的清白?”
“她在你家。”
“什么?”
阮红带着一丝歉疚,“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儿吗,其实我不是在给家人打电话,而是在和她说话。当时她就在你家门口,从十一点开始她就没离开过。”
“你留她在家里过夜?”
我难以置信,昨天夜里“鲛人”在我家里过夜,我竟浑然不知。
“第二天早上我亲自送她回来的。”
言语苍白,我只能用揪头发,原地转圈,来回踱步的方式表达繁复、凌乱的情绪。如果阮红说的句句属实,那么她的确没有作案时间,换言之,凶手不是她而另有其人。如此说来,阮红之前的假设合情合理,鳞片是凶手故意丢在凶案现场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警方视线。
我长叹息,缓解压抑感,“真是没有想到。”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浑身都是伤,我怀疑遭人非法拘禁。”
我绕开阮红大步往黑屋子里走,但进去以后又下意识地放慢脚步。小女孩的警觉性非常高,稍微一点声音都会将她惊醒。就像现在她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惊恐地望着眼前陌生的男人。可见阮红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在遭遇非法拘禁的同时,还遭人殴打、虐待,甚至是拔掉身上的鳞。
我微微抬手,落在她肩膀上。
那坚硬的鳞片真实,生动,若不是亲眼见过真的很难相信。
“告诉我是谁伤害你的?你从哪里来?你的家人在哪?”
阮红蹲在我旁边,手轻轻抚摸女孩的头,“她可能是哑巴,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说过。”
“我必须得让她开口。”
“你先别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阮红从一个破旧的帆布背包里翻出这张褶皱的劣质画纸,上面有一副用蜡笔勾勒出来的抽象画,色彩诡异,线条凌乱而且粗糙,画面中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怀里面抱着一个什么东西,背后还有一颗孤零零老树,树旁边是一座插着草的孤坟
阮红猜测,“她可能是在用画代替自己的声音。”
我出主意,“那就想办法让她把知道的都画出来。”
13,另有隐情()
县不远处是一条晚宽阔的大江,周围山中又布满了湖泊,所以,即便是夏天,夜里也会有一丝丝的冷。女孩受了伤,我也不忍留她在这里忍饥挨冻,便决定暂时将她带回公寓再做打算。
我亲自给她做了一碗面,看她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面多少有些难过。
已经是凌晨。
在黑夜的衬托下屋内的光愈发明亮,她身上纵横交错的伤暴露无遗。半脸的鳞片,半脸的血迹,让她看上去是又可怜又吓人。但她的眼睛很大,五官很立体,如果不是因为这种怪病,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她有名字吗?”
“不知道。”
“那就给她起个名字吧,就叫小鱼。”
阮红帮小鱼冲洗了身子,又对她的伤口进行包扎处理,直到四更天时才各自睡去。
天一亮我就去了局里,谨记着阮红对我的嘱托,没有和任何人提小鱼的事儿。所以他们还人为凶手是“鲛人”,东奔西跑着。我并非故意要隐瞒真相,就像阮红决定带我去见小鱼时,她有顾虑,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顾虑。周全考虑,暂时不做声张。
小鱼不是凶手,说明凶手另有其人。
我想起昨日和陈思说过的话,凶手之所以能在他们眼皮子地下作案,最主要是他巧妙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而他之所以顶风作案,目的只有一个,暴露“自己”从而获得新的“生机”。通俗易懂一点,凶手想趁此机会让小鱼的黑锅背的更彻底。
阮红说,她和小鱼是在山里偶然遇见的,当时小鱼浑身伤痕累累,就像刚逃难回来。我是不是可以想象成,她刚刚摆脱凶手的控制?如果真是这样,凶手一定很担心自己的罪行暴露,必定会到处找小鱼。想到这,我给阮红发了一条短信,让她和小鱼好好待在公寓里,不可出门。
半钟头后,我来到这个荒凉破败的小村子里。
陈思在村子里守了快两天,仍旧是一点的消息都没有。当然,他注定将不会满意而归,因为“凶手”现在就住在我家里。相比之下,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村长的下落。我可是听说受害人遇害的那天夜里就找不到人了,并且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好好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不奇怪吗?
找到陈思,我说,别熬了,凶手不会回来了。
陈思很有毅力,死不放弃。
我无可奈何叹着气,就算抓到又有什么意义,鲛人就一定是凶手吗?陈思不懂我的意思,我便把昨夜阮红的话给她重复了一遍,鱼鳞又不是羊什么的毛说掉就掉,除非是凶手故意留下线索,所以每个现场都有鱼鳞?换个说法,我不相信凶手每次都这么大意。
还有就是那枚血脚印也是十分可疑。
通常现场脚印都是凶手粗心大意时所留,因此脚印一般不会很完整,但我们采集到的脚印却一点残缺都没有,人为伪造的痕迹很明显。
和陈思说完这些以后,我一方面暗自庆幸,一方面也自我检讨。
在勘现场、验尸体的过程中,我的确疏忽了很多的细节,没有合理、逻辑性地去分析线索,以至于没有将案情吃透。听了我的话,号称辣手神探的陈思也自惭形秽地抓耳挠腮,自省说,往往看似合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