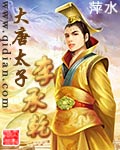干妹子-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夜之间家里就出了这么大变故。槐叶死了,宝宝跑了,这噩耗就像一声炸雷劈在了王富才头上,当时就把他击懵了。高月娥咒天骂地,连王富才的八辈先人也不放过。水仙当然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她没想到槐叶会死。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她感到愧疚,还有那么一点同情。她眼泪汪汪地劝公公别着急上火,劝婆婆别生气伤身,完全表现了一个媳妇应有的本分与贤良。
村里的大事莫过于红、白二事。白事比红事更隆重、更讲究。槐叶是干下了那等丑事才自尽身亡的,就不能按一般的风俗习惯办理。按照惯例,只给她娘家照会一声,挖个坑埋了就算了事。勾庆成不是一般人,他是村长,是老板,是大款,是头面人物,因而也就不能草草了事。
老婆跟别人睡了总不是光彩事。尤其嫂子很小叔通奸,村里有个形象的说法:鼻涕流进嘴里。这种事丢人败兴羞先人,因而也就不敢张扬,生怕别人知道。勾庆成却硬要守灵三天,给副村长四毛留下一句话:看着办。
村长家办丧事,副村长就是当然的总管。平日里,大小事都得村长勾庆成点头,今天总算让四毛这二把手做了一回主。“看着办”就是酌情而定,既要顾及勾庆成的面子,又不能显摆。四毛合计了一番,将灵堂就设在前院里,靠墙搭了个布棚。棺材停在布棚下,灵前一张桌子,桌上摆着几样吃食与果品。看起来面子上过得去,说起来有这回事,也真真地显示了副村长四毛的精明。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txt电子书下载
按照常理,勾庆成不能去报丧。他是怕槐叶娘家人来闹事,就决计亲自走一躺。
槐叶娘家在槐树凹,离桑树坪20来里,勾庆成没把车开进村里,就停在了村外。他是怕槐叶两个弟弟把他的车砸了。
勾庆成一进他丈人郑老三的家门,两腿一弯就跪在了当院里。哭诉着把槐叶喝了卤水,为啥喝了卤水说了一遍。
郑老三傻呆了。他老伴当时就晕了过去。他的两个儿子骂骂嚷嚷,扑上来就抓住勾庆成就要打。郑老三喝住了:先别动手,叫他把话说完。
勾庆成鼻涕眼泪地:爹!娘!你们难过,我也揪心。两个兄弟惩治我,我认了。槐叶走了,咱这亲没断呵!你二老还是我的老人,我给你们养老送终。槐叶的事就是我的事,二位兄弟的婚事我全包了。实在不行,我这条命就赔给你。我亲自来报丧就是把能心里话对二老说说,该咋着,你二老看着办吧!说完爬在地上呜呜大哭。
郑老三毕竟久经世故,他忍住痛憋住气暗自思忖。平日里他也风言风语听说了女婿一些花花事。现在这事不希奇,那些年轻人、村长、老板,一有了钱,哪个不是这样。没有真凭实据,他也就不好过问。槐叶跟宝宝却是被抓住了,为这事女婿打她也不为过。槐叶死不是别人害的,是她自寻短见。勾庆成也吃不了官司,打他几下出出气又能咋的,不光把这门亲打断了,还结下了怨。打打闹闹只能把女儿的丑事越扬越臭,他那老脸更没地方搁。再者,勾庆成今非昔比,留一条路总比断一条路强。他吸溜了两下鼻子,用袖子抹一把老泪:你娃说得天花乱坠,我心里有数。槐叶死是她自寻短见,可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人死不能复生,入土为安。我先不跟你计较,日后咋样对郑家,就看你娃了。
勾庆成趴在地上就磕头:爹,你是明白人,我也不会办糊涂事。我说过的话句句算数。
郑老三两个儿子不干:爹,我姐就白死了!郑老三拉下脸来:少言传!我活着就抡不到你们说话。送送你姐夫,他还忙着哩!
勾庆成:我是来接你们的,不见槐叶最后一面咋行。
郑老三摇摇头,长叹一声:不见了,再见也活不过来了。便抽泣起来。
要不叫两个弟弟跟我去。
谁也不去。你看着办就是了。
勾庆成爬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站起来:两个弟弟,你们可一定要来呵!我等着哩!说着就出了门。
郑老三不是不想见闺女最后一面,是因为他闺女偷汉子,而且偷的是她的小叔子宝宝
——一个傻子。他实在没脸踏进桑树坪,没脸见人。他知道自己闺女是正派人,她不会轻易跟一个傻子好。可是,不管因为啥,干下了这种事就输了理,也丢尽了人。他还有啥脸面跟人家说长道短抡是非。就觉胸中像是揣了块石头,憋得他喘不过气来,扯起嗓子:老天爷呵——
015。桑树坪夜话 (十五)
十一
公路上小车一辆接一辆。县里那些平日和勾庆成有过来往的头头脑脑们紧着朝桑树坪跑。
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却也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勾庆成家是白事,来宾们不咸不淡地安慰几句就抬屁股走人了。这一辆辆小车,一个个大腹翩翩的领导,使村里人真真切切看到了勾庆成的实力和能量。他们对于槐叶的死也决不会在人前公开谈论,天下没有那么傻的人。
勾庆成白天轻易不露面。具体活有具体人干,有他没他一个样。到了晚上他才出现,一付十分疲惫的样子,啥也不说,一个劲给办事的人递烟。赶到夜里12点左右,就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回家,他自己守灵。客随主便,谁不图个轻闲。因而一到后半夜,前院里就剩下勾庆成自己。
勾庆成把前院的大门上好,再仔细地查看一番之后,就到水仙屋里去了。
夜,依然黑暗、沉闷而幽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王福才却睡不下。宝宝跑了,白天他不敢找,他怕惹勾庆成生气。只有在更深夜半之际,才从小楼里悄悄溜出来。他知道勾庆成没打着宝宝,也知道宝宝光着身子没穿衣裳,更知道宝宝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他怀里揣着两个馍,小心翼翼地捉住,生怕自己不小心弄丢了。村里村外,沟上沟下,岭前岭后他都找遍了,连宝宝的影儿也没见着。他弓着腰,探着头,强睁起昏花的老眼。一边走,一边找,一边轻声呼唤:宝宝——宝宝——这颤颤巍巍,悠悠扬扬的呼喊声,在渺无人迹的暗夜里,在寂寥空阔的旷野上像叫魂一样。隐森森、凄惨惨,好不瘮人。
宝宝从家里跑出来并没有跑远,他也跑不远,更不知该往哪儿跑。只知道哥这回是真得火了,若不是逃得快,早就被哥敲死了。他只顾朝前跑,实在跑不动了才站了下来。四处一片漆黑,他分不清哪儿跟哪儿。深秋的山里本来就凉,“嗖嗖”的夜风像钢针一样,成把成把地扎在他身上,刹时就起一身鸡皮疙瘩。在幽暗的天光下,他看见身边的地里有一堆玉米秸子,他想都没想就钻进去。哦!比站在风地里暖和多了。冷风依然携着寒意,顺着玉米秸子缝隙直灌进来,吹得他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只能尽力地蜷曲起身子,再冷也比叫哥敲死强,死了就再也活不成了。
宝宝藏身的这堆玉米秸子就在村口的路边上。王富才来回路过这里,他走出村很远了才呼叫,宝宝焉能听得见。
宝宝钻在玉米秸里,夜里还好过些,白天一动都不敢动,他怕哥看见了把他敲死。睡梦中他听见有人喊。睁开眼仔细一听,是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在唱歌,他哑然地笑了。
016。桑树坪夜话 (十六)
醒了就睡不着了,他想起嫂子。嫂子是哥的媳妇,哥不会敲死她。哥对嫂子一定像他对水仙那样。他又想起跟嫂子睡觉。那滋味真好,就像吃蜜糖,吃了还想吃,咋也吃不够。一阵冷风恣肆地吹进玉米秸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身子蜷得像个刺猬。他又想起来,睡着了就不冷了,也不饿了。他闭上眼睛,心里说:睡,睡,睡……却咋也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就越觉得冷、觉得饿。再冷再饿他也不敢出去,就那样等着。等什么?等谁?等到啥时?他不知道。肚子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他只得把肚子搂得更紧。
冗长的夜幕覆盖着大地,桑树坪沉睡在梦鼾之中。村子里只有勾庆成家的后院里还亮着灯。
夜里12点左右,勾庆成就把办事的人都撵回了家。插好前院的门栓,灵棚里还剩下一只小灯泡将就地亮着。他推开二门,进到水仙屋里。
勾庆成疙猴在床边,水仙爬在他背上,两人撩逗着床上那娃儿。他脸上漾着喜悦,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伸出一手食指轻轻地在娃儿脸蛋上一碰:叫爹。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好看的txt电子书
娃儿睡着了,脸蛋儿被人碰了一下,就有了无意识的反应,小嘴稍稍一瞥,一付很是委屈的模样。
娃咋不叫?他问。
叫了。
我咋没听见。
我听见了
啥时叫的?
刚才。
刚才——刹时他就回过味儿来,猛地转过身,两手便向她腋下滑去。她“咯咯”地笑着,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在床上滚来滚去。他倏地爬在她身上。她两手勾住他脖子。两个人一动不动,就那样紧紧地抱着,仿佛一幅定格了的画面。
良久,他听到她一声轻微的叹息。她这一声叹息也是他的心声。槐叶死后的这两个夜晚,是这一年多来他们最舒心、最惬意、最幸福的两个夜晚,尽情、尽意又尽兴。好象他们已排除了所有的障碍,终于如愿已尝了。一觉醒来又回到现实中。这样的好景能维持多久,他不知道。但他希望这令人陶醉的时刻永驻,时间不再前进,日头从此不再升起……
她轻摇他肩膀:傻子到底哪儿去了?
他鼻子里一哼:管球他,死了才好哩!
那就称你心了。
不称你心?他笑着反问。
她嗔他一眼,张开小嘴咬住他耳朵,轻轻的……
槐叶的灵柩停放两天了,明天就是第三天,就要出殡。
这天夜里,陡然间狂风大作。呼啸着满山遍野地横冲直撞,肆意地敲打着房屋门窗,把人们从睡梦惊醒。怒吼着,号叫着,向人们展示它的淫威。
藏着宝宝的那堆玉米秸轻易而举地就被狂风荡平。他赤条条地猴在那里,身子不住地打颤,牙齿磕地“咯咯”作响。狂风、寒冷、碌碌饥肠驱赶着他,像只夜猫似的探头探脑朝村里摸去。
宝宝最熟悉的还是前院喂牲口那屋,除了这儿他也没处可去。大门插着,他就从墙上翻进院里。这会儿他突然变得聪明了,进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门栓,他觉得这样保险。一转身,他愣住了;院里咋搭了个棚子,棚子里放口棺材,棺材前面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吃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吃的就往嘴里塞,直塞得再也填不进去了才停住手。肚子暂时安顿住了,冷得感觉就更明显了。他蹑手蹑脚朝喂驴那屋走去。后院里传来大狼狗“汪汪”地吼叫声,他急慌溜进屋里。
屋里严实,没有风,还有毛驴急呼出来的热气,宝宝顿时就感到一种舒适。床上的被褥和平时穿的衣服不知哪儿去了,只剩下一张光溜溜的床板。他看见了墙角那堆麦草,欣喜若狂地一头就钻了进去。
017。桑树坪夜话 (十七)
这两天人们只顾忙别的,竟忘了这头驴,食槽被驴儿添得净光。驴儿见主人回来了,就在草堆里,高兴地仰起它那特号的把式长脸,打着响鼻。半晌还不见主人喂草,驴儿等急了,就扯起嗓子“呜啊,呜啊——”地叫起来。
勾庆成跟水仙正热乎着,一翻身就坐起来。他先是听到狗叫,不一会儿驴又叫起来。一般来说,驴夜里不叫,夜里驴叫就不正常。莫非有人偷驴?勾庆成倒不是在乎这头驴,这贼人也太胆大妄为了,竟然偷到了村长头上。勾庆成麻利地穿上衣服,出了屋。悄悄地开了二门,朝牲口房走去。
夜深人静之时,驴叫声不压于高音喇叭,王富才也听见了驴叫。他是出去找宝宝,没找着返回来,走到楼头就听见了驴叫。他忽然想起两天没喂驴了。本来他不想管,人都没了,还要驴干毬哩!又觉得这不会说话的畜生也是一条命,总不能把它饿死,就从楼头绕到前院去喂驴。
勾庆成来到喂驴这屋,仔细地看了一遍。屋里除了这头驴,再没有第二件活物,但他还是看出了异常。驴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神急促不安,蹄子刨地,不住地打着响鼻……若没有别的东西惊扰,驴不会这个样子。他警觉地搜索着屋子里每一处角落。突然,他发现那堆麦草微微在动。从那动弹的样子,他判断草堆里藏着什么。他不敢肯定藏着的是人还是动物,顿时就感到一阵紧张,顺手操起了立在门后的三刺麦叉,大喝一声:出来!突然,麦草不再动了。他又大声喝道:不出来戳死你!
宝宝这才慢吞吞地钻出麦草。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头上身上沾着一些麦草,两臂哆哆嗦嗦地抱着前胸,黑乎乎的雀儿耷拉在腿裆里。
勾庆成一见宝宝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心里就有了几分怜悯。他毕竟和这个傻子一起生活了20年。刹时,这个**裸的人在他眼里就变得面目狰狞。就是这个面目狰狞的人跟他媳妇槐叶通奸,给他戴上了绿帽子。还占有了他的心上人水仙,当上了他儿子的爹……这种怨愤顿时就变成了嫉恨,变成了仇视。他认准了,只要眼前的这个人存在,他跟水仙就永无团圆之日,父子也永远不能相认……他眼一闭,牙一咬,挺起麦叉刺过去。宝宝只轻轻地哼了一声,就软绵绵地跪倒在麦草上。
十二
王富才来到前院,大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院子。一抬头,就见勾庆成拽住什么从牲口房里朝外拖。他觉得奇怪。半夜三更勾庆成干啥哩?他一侧身隐蔽在门墙后的黑影里。
前院里亮着灯,虽不十分光明,却也看得清楚;勾庆成拖的是个人,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勾庆成把这人拖到灵棚里,掀开棺材盖,抱起了他拖的那人。
灯光下,王福才看清了;那浑身净光的人是宝宝。他那颗心从嗓子眼儿直往外蹦。他看得真切;宝宝软得像根面条儿。身上几个窟窿,鲜血从窟窿眼里“咕咕”地朝外冒。勾庆成像填麻袋似的把宝宝塞进了棺材里。王富才脑子里“嗡”地一下;宝宝死了,被勾庆成弄死了。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道:畜生!畜生!他两眼一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