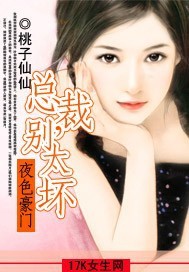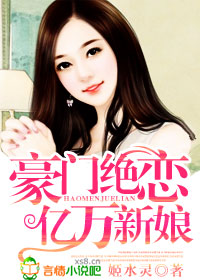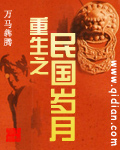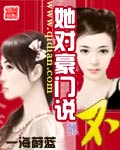民国大文豪-第1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正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所说:作家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扎米亚京对林子轩想要出版他的小说没有意见,很痛快的写了授权书。他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中国会受欢迎。
通过苏联的报纸,他看到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
他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知道在那种狂热的氛围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你在苏联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过离开这个国家么?”最后。林子轩询问道。
“我想还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亚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国内形势的好转,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没有拒绝林子轩留下的卢布,作为中文版书籍的稿费,他需要金钱来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购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亚京并没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国内走投无路的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申请被驱逐出苏联。
在这封信的开头他自称是“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他诉说了自己在国内的遭遇,处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被人恶意的攻击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结尾处,他说:“我申请和妻子一同出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走投无路,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被判处了死刑。”
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扎米亚京最终离开了苏联,定居在巴黎。
在回去的路上,林子轩进行了反思,文学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作家?
作为一位穿越者,作为一位依靠抄袭成名的伪作家,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是就这样混上一辈子,还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他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穿越以来,他就不断的成长,思想在不断的变化。
刚穿越的时候,他只想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不去理会别人的死活,所以他抄袭的无所顾忌,以赚钱和出名为最终目的。
后来,他认同了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家族的责任,就收敛不少。
他树立自身的形象,维护家族的利益,成为上海有名的士绅,参与到上海的发展中来。
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他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
与此同时,苏联的马克思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家们做出了决定,不承认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
他们认为这个论断并不科学,没有理论依据,只是一位无党派人士的突发奇想。
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在他们心中,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该由苏联的理论家来划分,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把文件归档,就此放下了这件事。
林子轩的名字和这些文件一起成为了尘封的档案。
这充分表明了苏联国内在这一时期的自大倾向,他们觉得自己的革命获得成功,就开始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指手画脚,认为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应该听从苏联的指导。(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六章 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
很多年后,在蒋京国的回忆录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林子轩的这次思想转变。
从扎米亚京的家里出来,先生一路上都很沉默,我想他是在同情这位苏俄作家的遭遇,但这种事情在苏俄相当普遍,我更为担心的是回到学校后该怎么办。
我一直劝阻先生不要和苏俄的颠覆分子接触,那样会惹来麻烦。
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今天的情况告诉学校的校长。
在学校里,教员告诉我们,要随时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
我想回去后一定会有人找我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
正当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先生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么?
我当然回答不愿意,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会被砍头,谁会愿意被砍头呢。
先生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我当时还年轻,不曾多想,后来想了想,才发觉先生想必在那时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想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每天比其他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来提醒这个世界。
第二年,先生便发表了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争议的小说《1984》。
这部小说让先生成为了半个世界的敌人,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我想这就是做一只有坏习惯公鸡的代价。
但正因为如此,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才值得我们的尊敬。
*****************
林子轩的确问了蒋京国这个问题。他也在考虑要不要把《1984》这部小说写出来。
《1984》和《蝇王》不同,《蝇王》只是寓言小说。《1984》却是政治小说。
《蝇王》讨论的是善恶的问题,更深层次则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1984》展现的却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世界。这是对政治制度的探讨和讽刺。
这本小说不仅会被苏联这样的国家禁止,由于小说内容具有煽动性和危险性,在西方社会也会被一些国家禁止。
在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大的抨击,甚至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奥威尔1949年出版了《1984》,1950年1月他就过世了,这是他的幸运,没有碰到之后《1984》遭受禁止和攻讦的遭遇。
林子轩还有很长的日子要活,所以必须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关键是他要不要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
他可以选择抄袭一些不带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同样能获得荣誉。
在后世。有位名叫王晓波的作家写了一篇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章讲了他在插队的时候遇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猪。
这只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这只猪很聪明,会模仿各种声音,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
它后来学会了汽笛响,和工厂下班的声音一样,从而惹来了麻烦。遭到了围捕。
但这只猪还是逃跑了,后来成了野猪,长出了獠牙,冷冷的看着人。
林子轩明白无论是有坏习惯的公鸡还是特立独行的猪。都不太见容于这个社会。
和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它们最大的罪过。
它们如果想要生存下来,需要把自身的个性和棱角磨平。变得平庸。
否则最终的结果要么被砍头,要么远离人类。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甘于平庸,想要保留个性。那就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因为坚持真理而选择喝下毒酒的苏格拉底,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的布鲁诺。
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坚持己见而被迫害的人,正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人类才能取得进步。
选择要不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子轩没有那么伟大,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内心里仍然是小市民的思想,只是觉得自己或许应该做点什么了。
回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和冯程程商量着回国的事情。
算起来他来到苏联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参观了列宁的墓地,看了不少莫斯科的古迹,在戏院里欣赏了芭蕾舞剧和几场电影。
特别是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可以说是默片时代的经典。
爱森斯坦把蒙太奇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是电影大师也不为过。
林子轩没有能见到这位苏联导演。
据说为了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献礼,爱森斯坦接到命令,正在外地拍摄表现十月大革命的电影《十月》,场面非常宏大。
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大多是革命题材,或者反应俄国农民生活的片子。
他们的纪录片很有特色,能拍摄出那种宏大的气势来,尤其是宣传军队的纪录片,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
这种纪录片会时常在影院放映,看多了还真能产生向往革命的热情。
苏联电影采取国有化管理,审查非常严格,上级下达命令才能进行拍摄,对于外国电影的引进更是谨慎。
目前的中国电影恐怕是没办法进入苏联市场了。
林子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遇到了曾经在巴黎见到的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
这位四川青年因为在法国被巴黎警察通缉才来到苏联,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上学,后来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安排学习俄语。
林子轩和他聊了聊巴黎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随着欧洲经济的衰落,工厂的薪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日子不太好过,举行过几次罢工,但效果不大。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这需要政府出面,筹集助学基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单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王名、博谷和张文天等人。
还有十几位广州国民政府要员的孩子,以及先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这些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中国的面貌。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校方举行了一场座谈会,让林子轩向学生们谈谈在苏联参观的感受,这是想试探林子轩对待苏联的态度。
1925年那场“仇俄联俄”的争论在中国国内造成不小的影响,中国留学生都有所了解。
他们也想知道林子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七章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座谈会在一间会议室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包括苏联的教员。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生活在苏俄会怎么样?”林子轩提出了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让在座的青年思考,这其实就是代入感。
想象自己是一个苏俄人,生活在这个国度,会过上什么生活。
“如果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的小说可能没办法出版,我的电影无法通过审核,我的产业会被收归国有,我或许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林子轩继续说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暗自捏了一把汗,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其他人错愕起来,他们没想到林子轩在这种场合会说的那么直白。
“我是资本家,在这个国家自然会觉得痛苦。”林子轩坦诚道,“为了生活下去,我可以改变自己,学着写一些表现革命或者赞颂国家的小说,拍摄革命题材的电影,甚至是进入政府,成为官员。”
在座的人疑惑起来,这是要向着革命靠拢么?
“改变之后我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这就是环境对人的改变,但这样我就感觉满足了么?不会痛苦了么?”林子轩反问道。
“我变得和别人一样,我分不清自己和其他人的区别了。”他忧虑的说道,“在莫斯科的街头,我看到所有人穿着几乎相同的衣服,露出相同的神情,我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区别。”
“你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青年起身高呼道,“打倒资本家。打倒资产阶级自由派。”
“穿相同衣服是人人平等的表现,消灭了阶级。这是社会的进步。”有人呼应道,“你这种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怎么能明白。”
“苏俄不欢迎你。滚出去。”有人叫喊道。
“我正准备离开。”林子轩平静的说完,走了出去。
走出会议室,他不由得露出了苦笑,在这里说这种话果然是自讨苦吃。
他原本还想讲的更多,却不得不中断。
他一直崇尚的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碰撞交锋,多元并存,从而产生多元的文学,如此文学艺术才能蓬勃的发展。
他还想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在苏联的见闻。
但他不会为了讨好这些青年而说假话。为苏联歌功颂德,这是做人的底线。
和来的时候受到的迎接不同,林子轩走的相当孤单,只有蒋京国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坐上火车,林子轩暗自松了口气,他还担心苏联当局会为难他呢。
看来不被重视也有好处。
冯程程担心的望着丈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事情她听说了,她怕丈夫一时想不开。
以往林子轩在国内大学演讲和讲课都会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