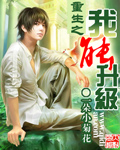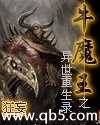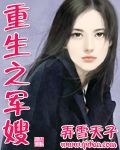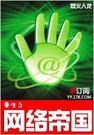重生之大明摄政王-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产量中心是在东北和北直隶,比如有名的铁岭,就是因铁厂而成名,现在是落在满清统治区内了。
著名的遵化铁厂,已经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
就是说,官营的铁厂宣告倒闭,负责官员全部丢了饭碗,然后朝廷把地给租了,得了银子去买铁来用。
在后世国企坐大的某朝,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奇景。就算是在秦汉唐宋,这样的事也是绝无可能的。
汉唐盐铁专卖,这些战略物资是牢牢握在朝廷官府手中的,各处设铁官,矿产发卖一条龙服务,盐铁之利,百姓商人是沾不得一点的。
到了明朝,官营铁矿倒闭,私营铁矿却是欣欣向荣,朝廷要向民间去买铁……这种事情,也就是在明朝才有可能了。
这原本没有大问题,但官营铁矿纷纷倒闭,私营铁矿在万历年间也受到摧残,这铁的产量确实是下去了。
而且,官营转民营,小规模的炉房多,嘉靖三十四年有规定,铁矿山场许其设炉,就令山主为炉首,每处只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俱系同都或别都有籍之人同煮,不许加增……其炉首即为总甲,每十人为一小甲,其小甲五人递相钤束,填写姓名呈县,各给执照。
就是说,矿区生产,不仅限定人数,还规定总甲和递保,否则的话,就会被府县卫所巡捕稽查,一旦有违反,一定从重治罪。
当然,王朝末世的时候,一切法令,皆成具文。所谓无主官山,只要能出矿的,就一定会有大量无籍流徒涌入,每年在秋收之后,纠集成百上千,然后分布各山,依山起,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最少数百人,在山掘矿,以此取利。
山主矿主收租税,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则利其雇募。
整条产业链,最倒霉的就是官府。
官矿和领官照的矿,朝廷有铁课或是有三十税一的矿税。
结果官矿全完了,领官照的也寥寥无已,派在各矿的矿监根本起不了作用,南方到处都是这种民矿,根本也不纳税,只是贿赂当地的地方官罢了。
这种矿,肥了私人,出产到底还不如当年官矿,而且这些年兵事增多,铠甲兵器等用铁的地方大增,不仅是官兵,流贼,东虏,都要用铁,所以这铁的出产虽逐年增加,但仍然远远不敷使用。
现在的铁矿,最大的集散地就在江南的芜湖一带,不仅有铁矿,还有出钢的钢炉,算是当时大明的独一份。
第一百六十一章 大明矿业(3)
这里出产的铁,每年是过千万斤的规模,行销天下,大明矿业最集中,出产最多的地方,以前是门头沟到遵化一带的铁厂,现在就属芜湖一带的民间矿业集团了。
眼前这伙晋间,在北方玩的转,收粮卖盐,走私战略物品,反正捅破天的事也敢做,也没有什么事是担不下来的。
但北方玩的转,南方就玩脱了,人家芜湖铁业是操控在南方士大夫和大商人手中的,这些人看到晋商就是一肚皮的火气,彼此是竟争对手,哪里会有好脸子给晋商们看?
现在的问题不是晋商被坐地起价,或是被卖高价,而是因为铁越来越缺,芜湖一带,北方商人给钱也买不到生铁,简单就是两个字:没货!
这其中原委,薛国观知道一些,有一些也不大了然,此时也只能皱眉听着。
一边的林文远是听的津津有味,因为贩盐,他们一伙和张守仁一起对大明的盐政有过推敲,张守仁曾经笑曰,这种制度十分稀烂,肥私人损公家,简直是蠢透了。
但现在这种时候,制度蠢了,才是他们的可乘之机。
这铁业也是这么稀烂,前小旗官现任千户官林文远听在耳朵里,这心思也是动的飞快。这件事,和浮山怎么联上关系,怎么运行才好?
他这边思索,那边薛国观也是开口了:“诸君的意思,老夫也是明白了。也罢,我会修书一封给凤阳总督,诸位要买多少铁,派人持老夫手书,去寻他设法就是。”
“如此大好,在下谢过阁老!”
亢东主似乎是一跃而起,声音也是十分欣喜。
范永斗也是紧跟而上,对薛国观大表感激之情。其余诸家晋商,自然也是有样学样。
“诸君请回,允诺的粮食数目,还望尽早运至。老夫倦矣,就不留诸君了。”
不论是薛阁老还是商人们,都明白对方是十分精明的人物,这些商人显然是被缺铁的难题给难住了,凤阳总督和薛国观的关系很近,而芜湖地界的大商人和士绅们怎么也要卖凤阳总督一个面子,他们买铁的难题也就是就此解决了。
激动之下,狐狸尾巴也是露出来一点,这么高兴的样子,显然是过来的时候就商量好这个盘口条件,就等薛国观同意了。
堂堂阁老,被一群商人挟持,还偏偏迫不得已就得同意对方的条件,而这些商人也没有丝毫的报国之意,京师粮价在他们心中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甚至有可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大粮商故意借着当前有利的借口,故意抬高粮价,亦非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夜漏更下,和商人们谈了这么久,薛国观实在觉得疲惫,也是没有心情再敷衍下去,自然就是开口逐客。
“是,请阁老早早安歇。”
亢少东最见机一个,别看是人胖,心思动的比谁都快。知道薛国观此时心里不是滋味,在这里呆久了,反而迟则生变,立刻就答应一声,施了一礼,转身就是退了出来。
第一百六十二章 垂训(1)
第一百六十二章垂训
一群晋商鱼贯而出,这边隔开间的书房里长随也是过来了:“林大爷,我家老爷倦的很了,要不是先前回过,断不能请你过去。若是无事,叩个头说几句好听的,就直接辞了出来也罢了……将来再来京,见面也是很容易了。”
相爷长随,那是何等身份,普通的州县也是没有资格听到这番话的。林文远待人亲和,自己出身卑贱,所以骨子里头就没有什么官身民身的成见,对这些下人也是平等相待,时间久了,加上大捧银子铺路,所以薛家这些人也不拿他当外人了。
就林文远拿到千户告身腰牌的时候,这些长随下人还凑了一桌,大家共饮相贺来着。
要不然的话,薛阁老是何等身份,哪里有“见面很容易的”这一说?
“生受了,”林文远出手是极大方的,一边往外走,一边就是一小锭银子塞在对方怀里:“夜沉了,一会从街市上买点羊脸肉,几个值下夜的喝点酒解乏。”
这也是常有的事,而且林文远说的十分诱人,那个长随笑呵呵的接了下来,就是赶上两步,在林文远前头引路。
“咦……”
一出门,正好是和范永斗撞了个对脸。
因为有在相府见面的情分,林文远也曾经去过几次范家商行,打听点物价消息,拉拉关系……浮山那边现在生意做的可不小,打交道的商行也极多。
利丰行这样的山东本地大商行和这几个晋商比……估计最小的晋商拔根毛也是比利丰行要粗上那么几分,真正要做大买卖,和这些晋商打交道也是不可免的。
不过范家到底是巨商,林文远身份差的远,浮山那边出的又是盐,山西的井盐可多的是,而且从甘肃一带的天然盐井还有大量出产,鲁盐想卖到山西那简直就是做梦,人家也不可能要,再物美价廉也不可能。
一个地方要保护一个地方的产业,除非是不产盐,否则的话,外路盐想进来,得罪的人就海了去了。
最底层的盐丁灶户,吃拿卡要的小吏总甲,坐地分肥的地方官员,包销包售的各路行商……这么一想,就知道这利益链有多大,不是吃撑了的,断不会在这种事上多事的。
没有利益,就没有交集,虽然范家也请过林文远吃酒什么的,不过只是当只苍蝇,在席间嗡嗡飞两下,也没有什么害处……
现在又在阁老这书房见到林文远,范永斗才觉得自己的判断出了岔子。
一件事得蒙阁老召见,可能是特例,再三再四的召见,那就说明,这个浮山来的小军官,应该是和薛阁老建立了某种私人联系。
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眼前的情形了。
不愧是商人,范永斗的反应快极了,当下先迎上一步,接着就是双手迎上来,执住林文远的两只手,低声笑道:“林老弟,这一阵不到老哥那里走走,是不是嫌上回饮宴怠慢了?这可真是冤枉老哥了……”
第一百六十二章 垂训(2)
然后就是絮絮叨叨,解释上回请客时的怠慢实乃无心之举云云……
这边范永斗忙活,那边亢家少东也非等闲,肥硕的身子猛闪过来,把范永斗挤在一边,脸上的肉也是挤的看不见眼:“林老哥,甭理老范,有空了到我那里走走,小弟独好美食,管你山中走兽,水上奇珍,反正世间有了,小弟我的厨房就得有……最近来了几桶辽东白鱼,我叫人烹调了,请你老弟过来,咱们一个外客不请……哦,叫上老范,三人同饮,说说笑笑品鱼鲜,如何,如何?”
这辽东白鱼是黑龙江一带的水产,大而鲜美,也没有刺,辽东沦陷之前是京师奇珍,皇室也没有多少活的可吃,毕竟道路太远,一路运送过来,到京师十条也难活一条,所以谓之以奇珍。
现在这个时候,辽东道路断绝,这厮是怎么弄到的?
这当然不能深究,林文远在京师久了,这些门道早清楚了,当下也是连连拱手,脸上笑意充足,应答声也是带着笑意:“两位大兄盛情,弟铭感五内,只是今日此来,却是来向阁老辞行来着……”
“怎地这就走了?”范永斗圆睁双目,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这太可惜了,不知老弟何时再回来?”
亢少东走的就是柔情路线,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
林文远在心里长叹口气……自己在京师经营的这么多门路脉落,交给别人怎么处?但以后再有差遣,难道还是自己跑来?
练兵带兵,才是他的挚爱啊……
“弟奉命回,委实还不知道何时再诣京师,不过,只要来京,一定拜会两位东主。”
“好,到时候我扫榻相迎!”
“我倒履相候!”
两个商人都是情深意重的模样,又是和林文远敷衍了几句,直到长随催促,这才松手放行。
这副模样,当然是恶心巴拉,实在是叫人觉得不适,不过在一边的几个晋商倒是看的津津有味的样子,有一两个甚至也想上来结识,不过在薛国观的书房门前,亢少东和范永斗是旧识,打个招呼还没有什么,要是真的寒暄说笑起来,也是太不恭谨了,当下只能站着不动,只是向林文远点头微笑,聊以致意罢了。
“叩见阁老!”
林文远现在还只是个千户,五品官儿,和自己以前比那是天上地下了,和阁老比,还是蚂蚁和大象的差距。
不要说他,就是张守仁来了,从二品的武官在此,也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叩头,不要说张守仁,就是左良玉这样的加左都督的一品总兵官,在这里也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跪下。
在大明,武职官确实是太委屈了一些。
“哦,你起来。”
薛国观的眉宇间满是倦色,刚刚和商人的一番交结实在是很耗精力的……大约薛国观也没想过,自己宰执天下,居然还要和一群商人谈生意经,这他娘的真是从何谈起?
经此一役,他和人说话的兴趣缺缺,而且手头还有不少事要做,看看天色也不早了,早朝就算不必上,入值内阁的时间也不便太晚,宰相晏起,实在不是好名声哪。
当下先吩咐一句,接着便道:“林哥儿,你即将回浮山,老夫也没有什么要吩咐的。唯有你带话张大人,着他好生效力,他的功名前程,都是在马上厮杀得来,别的事,太过取巧了的话,要少作不为,你懂我的意思没有?”
林文远当然是懂了,薛国观的意思就是张守仁的这一次提拔是超迁越次,已经算是十分讨巧了。底下就好好好效力,多做一些实务,最好是立下战功,文人养望可以猫着不做事,最多讲讲学,读读书,武夫想要更进一步,却得实打实的做出一番成绩来,这当然不公平,不过谁叫武夫在英宗一朝落败亏输,没斗过文官们呢?
当下也只能恭恭敬敬的叩一个头,以示自己完全明白,并且会将原话带给张守仁。
“唔,林哥儿你自己也要好自为之,将来做一番事业,老夫观你聪明有余,人也是仁厚的底子,人生在世,得意只是一时的事,凡事多留退步,则人皆敬服,办事反而要容易的多了……临别之时,老夫就是这番话,听或不听,也是在你了。”
说起来明朝的规矩实在很多,光是称呼上就是很多门道。比如这大人之称,要是你见了比自己官大的官,一声大人,肯定就是往死里得罪人了。
得加敬称,老大人,老公祖,老父台,然后就是中丞、军门、制府等尊称,对阁老一级的,则是称呼更加尊敬。
称大人的,则是上级称下级的称呼,什么张大人李大人,就是后世小李小王小张的称呼,上级称呼下级没什么,但你能想象一个下级大大咧咧的称自己上司为小王吗?
象薛国观原本该是用林大人称呼林文远才对,但以现在的称呼,就是有点长辈训诫晚辈的意思了。
这种亲近,可不是钱能买到的,还是林文远数次入相府,答对从容,并且展露出优秀的素质……说起来他原本就是一个货郎,有点小聪明和小见识,但哪里够资格在相爷面前显摆?
功劳当然得算在张守仁头上,林文远在张守仁跟前那么久,谈吐,见识,风度,都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文人的聪颖博学,却无头巾酸腐气,有武人的磊落和勃勃英气,却无武夫的粗鄙气,这样的人,以薛国观的见识,当然知道是难得的人才,所以动了爱才之念,称呼起来,都是以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