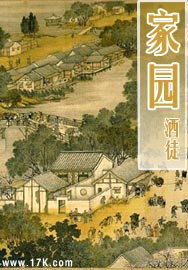枯草与烈酒-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肖烈,你知道吗?放在过去,我是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的。当然了,你也看不上我。”
卫澜点了一根烟,也给肖烈点了一根。
她的这句话里,重点在“过去”上面。过去,她是那么一个人,肖烈可以想象。一个纯纯的,傻傻的,为了爱情盲目奉献牺牲的,她当然看不上他这种人了。
而现在不同了,肖烈从她的眼神,动作上都看得出来,一个人把心放开,把一切视为无所谓,这些,都看得出来。
卫澜,她现在刚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她没死成,她还活着,怎么活着,怎么在他身边活着,恐怕是她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这事儿对于卫澜来说却简单的多了,因为她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从见到肖烈开始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处于了一种『裸』。体状态,她从不在他面前假装,虚伪,客套,等等都没有。她懒得和他多费唇舌,懒得动脑细胞,这个她,是卸下了所有包袱,所有伪装的她。
很有趣,很可怕,不是吗。
卫澜夹着香烟,呼了一口烟圈出来。头发披散双肩,一种颓废,一种诱『惑』,别有风情。坎坷,苦痛,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代价昂贵的化妆品。
她的声音带着慵懒,带着疲倦,“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单纯,心里眼里就能看见那一个人。”
“他对我很好,他单纯得像一张白纸,他的世界是纯白『色』的。”
“他追求我的时候,就是个大男孩儿,很不成熟的男孩儿。为了能有人陪他吃饭,陪他共度四年大学,让他高兴,让他恋爱,他也不会轻易和我分手。”
她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肖烈不置可否,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那种男人了解男人的了然。
“也是一个经历,好坏都有它的意义。”
她又笑了,“肖烈,今天的你,真不像你。这话是你说的么?”
“那我应该什么样?”
他抽着烟,青烟弥漫在他面前。
她用手指轻轻点着他的方向,“你啊,是个变化多端的妖怪。”
这句话让肖烈笑了起来。
他深深吸了最后一口烟,摁灭了烟头,“我是妖怪,你是什么?”
“我?”她低了低头,“我什么都不是。”
她的烟从鼻子里冒出来,女人,不该这样吸烟的。
肖烈看得出来,她喝多了。她半眯着双眼,看着夜空,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倾诉,让人的情绪很难硬起来。他们两个都是软的,难得的软绵,难得的放松,放纵。
卫澜更愿意说这是放纵,管他呢,既然还活着,为什么不放纵一次。如果最后都是殊途同归,那么这第二次生命,她不想再考虑那么多。
抽完最后一口烟,火星灭了。他们两个陷入了一片静谧祥和的黑暗。
肖烈的打火机亮了一下,又灭下去,他并没有点燃那根香烟。
帐篷敞着口,只『露』出挂满星星的夜空,画框点缀一般的树丛。
“肖烈,你有没有爱过别人?”卫澜抱着膝盖,头枕着手臂,轻声问他。
“我要是说没有,是不是显得特别没劲。”他说。
他的脸一半隐匿在黑暗中,一半在月光下。是岁月和一切都对他太好还是他把自己保护得这么好。这个保存完好的男人,明明就有伤痛走过的痕迹。
“你是很多女孩子会喜欢的那种类型。”她看着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
他笑了一下,转头迎着月光,而后又是一半精雕细刻的面庞看着她。
卫澜被这样的一切感染了。不是感动,是感染了。
她的笑容温婉。她第一次这样对他笑。
她醉着,这样的醉态给她平添了许多妩媚。
肖烈手里的打火机一下一下,明明灭灭的。他们彼此注视着,直到打火机再没亮起来。
他放下打火机,靠近了些。拨弄她的头发,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是谁的错,是谁的蛊『惑』。卫澜想起了张宇的一首歌《月亮惹的祸》。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肖烈吻过来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
☆、第28章()
卫澜望着漫天星空; 陷入梦境一般。
在他亲吻她脸颊的时候; 她说:“肖烈,我不想走了。”
不想走了。
这是个没有人想去细究原因的话题。
肖烈笑一笑; 『摸』『摸』她的脸,“还好我是个有钱人。”
卫澜也笑了,他们之间; 这样就好。一个出钱; 一个出人。
“你能抱抱我么?”卫澜说。
他们没有再亲热下去,卫澜忽然觉得醉得累,很想睡觉。在肖烈的怀里; 她很快就睡着了。
这个晚上,他们相拥而眠。
卫澜起来的时候有些头痛,昨晚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
回头看他的脸,她回忆起昨晚他的温度和味道。
不是梦; 是真的。
白天,他们又去了那个包子铺吃的包子,吃饱喝足了; 肖烈收了帐篷,卫澜帮忙把东西一件件放回车里。
肖烈收好了帐篷; 发现卫澜手扶着后备箱,面『露』难『色』。
“怎么了?”
“你还有多久?”
“收拾完就走。你去把毯子收了。”
“不行; 你收。”
她直愣愣地站着,肖烈挑了下眉『毛』,“那你等我一会儿。”
等肖烈东西都收拾好上车的时候; 卫澜已经系好了安全带,等了一会儿了。
肖烈注意到她屁股底下垫了衣服,他忽然意识到那是他的上衣。
“你——”肖烈才要说话就被她打断。
“开车,这衣服不能穿了,找家超市,帮我买点东西。”
肖烈已经知道她要买的是什么了。
等他真正站在超市货架前头的时候,他有点后悔,怎么没问她需要什么牌子的。这一排排,又是粉的又是蓝的,有什么区别。
他正挠头,身旁走过好几个女学生,看他站那儿有点不敢买了。
在这里站着的确很奇怪,被人当变态一样参观了好一会儿了。肖烈随便拿了一包去收银台结了账。
收银员是个女孩子,好心提醒了他,“你确定你要买的是护垫?”
“什么?”他哪知道那是护垫啊。
收银员说:“你女朋友是想要买卫生巾还是护垫啊?”
“她……她不太方便。”
收银员笑了,“那不是这个,你等一下,我帮你换。”
“好。”
肖烈这辈子也没做过这样的事。
他拎着黑『色』袋子回车上的时候,卫澜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不但没表示感谢,反倒埋怨了,“怎么这么慢?”
“下次自己买,又大又小的还是人帮忙换的。”
“换的?那你原来拿的什么?”
“你到底用不用?”
“哦。你外套借我一下。”
肖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得寸进尺,毁了他一件上衣还不够,还得搭一件外套。
这种事,争执没有意义,女人是很麻烦的。
卫澜披着肖烈的外套,去了kfc的卫生间处理好了。
回来的时候,她好像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靠在椅背上,欣赏街景。从市区到城郊,这条路很长的。出神,胡思『乱』想,时间倒是过得特别快。
到了院子里了,她还没想起要下车。
“喂,到了。”肖烈提醒道。
卫澜解开安全带,“我们还会在这里住多久?”
肖烈拔了车钥匙,嘴角翘了一下,“你不是说不想走了么。”
“我是这么说的,但我没说一直住一个地方。”
这话是昨晚上亲热的时候说的,卫澜没看他,他也没看她。各自收拾好了下车去了。
肖烈把钥匙抛高了又接住,没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卫澜进屋去了。张婶儿乐呵呵地和她说话,讲了些女儿和儿子的新鲜事。
肖烈把小六叫过来,帮忙把车里东西都给收了。
晚上,卫澜和张婶儿在厨房里一起忙活,张婶儿大张旗鼓做了十来个菜。卫澜只好尽力帮助。她不想白吃白喝让人伺候。可同时就又有了献殷勤的嫌疑。
张婶儿说今天是肖烈生日。这功劳一半归她。让肖烈得意,可不是她的初衷。
肖烈一时没得意起来,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天是他生日,他比任何人都意外。
他对张婶儿表示了感谢,对小六表示了感谢,对所有人表示了感谢,唯独没感谢卫澜。
只有张婶儿给卫澜说好话,说这晚上给小卫累够呛,做了好几道菜出来,还把手给扎了一下。
“一会儿给我看看,我那儿有『药』。”这就是肖烈的回答。
张婶儿已经笑逐颜开了,好像这就是给卫澜的认可和感谢了。
六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吃喝喝,倒也热闹。
昨晚喝了不少酒,今天又有酒。不过肖烈不允许她喝了。
还没等酒局开始,肖烈就命卫澜到他身边坐着,专门给他倒酒。
卫澜想起,他们之间是有过约定的,他不让喝酒的时候,她不能喝。
不过张婶儿想到的一定是另一个层面。她下桌的时候拍了拍卫澜的肩膀,好像是欣慰的,看,人家小肖知道你不舒服,这么关心你,体贴你,好好儿的。
所有人都误会了,只有她和肖烈两个人知道,他们之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之间是什么,她说不清楚,也许,肖烈会给出一个最准确的答案——情人。
买来的情人而已。
肖烈高兴起来也就那个样子,乐呵呵的。多余的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张婶儿和小六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
吃完了饭张婶儿就去歇着了,年纪大,跟年轻人可耗不起。小六和其他几个伙计与肖烈痛饮到深夜。
小六这人平时老老实实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会儿喝多了酒,话就多了起来。和肖烈天南地北的扯。大家都醉得很高兴,醉得很到位,都喝大了,唯有肖烈还很清醒。
喝到最后,小六就差倒地不起了。酒局没有持续太久,就各自回去歇了。
时间晚了,张婶儿已经睡了。卫澜自觉地扮演了张婶儿的角『色』,头发随便一绑,撸了袖子就开始收拾厨房。
肖烈还在酒桌上坐着,对着满桌子狼藉抽烟。
卫澜来来回回的收拾桌子,像个勤劳的小主『妇』。
张婶儿主张不要浪费,每餐饭菜的量都掌握地刚刚好。所以一顿饭下来,碗盘基本是干净的,这也就造成了很大的工作量。卫澜一个人洗了许多碗盘,腰有点酸了。
“你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么?”卫澜把碗筷收进碗橱,劳作的空隙随便找话来说。
“不知道。”
“张婶儿他们对你真好,还给你记着生日,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实意对你的。”
“你呢?”
卫澜往抹布上挤了些洗洁精,『揉』了两下,“我怎么了?”
“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你想听我说什么?”
卫澜没有停下忙碌,肖烈兀自笑了一下。对她,不该有什么要求的。
他想听什么,告诉她一声,她心情好的话,会说给他听的。
“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
“不是?”听了这句话,卫澜才转过身来。
她的头发扎得很松,有点『乱』了。厨房暖『色』调的灯照着她的脸,没再那么惨白惨白的。她的目光盈盈的,像是有水在里面。
“不是。”看着她的眼睛,他说。
“那怎么回事?”
“统计员工信息的时候,我随便填的日子,有心的,可能就记住了。”
“哦,那是哪天啊?”她转回身去,继续忙活。
“说了你也记不住。”
其实,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罢了。
卫澜回过头,发觉肖烈已经起身离开了。每当这个时候,卫澜就能隐约看见肖烈隐藏在心底的情绪,可他从不正面给任何人看。
收拾厨房时间是很长的,等卫澜完工终于回房的时候,肖烈来敲门了。
刚才没见他醉,这会儿却有了醉态。卫澜皱了皱眉头。
他一只手支着门框,一只手『插』着兜,腰弯着,重量好似都放在了胯骨上,眼睛红红的看着她。
“有事儿?”她有些警惕,这个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点点头。
“跟我来。”
他脑袋一偏,直起身子,在前头带路。
卫澜跟他进了房间,他却甩给她一件衣服。
他简直除暴,把那衣服扔在她脸上了。
卫澜扯下来一看,是那件粗布上衣。总拿这破玩意来折磨她,明知道她不会。他就是在刁难她。
“你就在这儿,缝好。”肖烈手指向着地面说。好像是一个在惩罚犯了错的孩子的家长。
“现在?”
“嗯。”他眼神『迷』离,点点头。
看见他桌子上摆着一排的啤酒罐,卫澜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越来越醉了。他还在喝。
这个时候,跟这个不正常的人争执这些没意义。
卫澜也不反驳,捡了针线拿起来就缝。针线原本就放在明面儿上,可能是他早就想好了要折腾她,专门为她准备好的。这个人为了折磨她,也真是尽心尽力,费尽心思。
卫澜一边缝一边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你刚才没喝够啊?”
“别说话。”
卫澜瞧他一眼,闭嘴了,不说话就不说话,谁愿意搭理你似的。
屋子里静悄悄的,他滋溜滋溜喝酒,她一针一线地劳作。
“你不是手指头被扎了吗?在哪儿?”他忽然问。
卫澜没吱声。
“你聋了?”他撇了一个花生粒过来,那么准,就打在她脑门上了。
“不是你不让我说话么?”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
卫澜缝好了衣服,拿起来抖了抖,抻开,拎高给他看,“行了吗?”
他没吱声,卫澜把衣服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