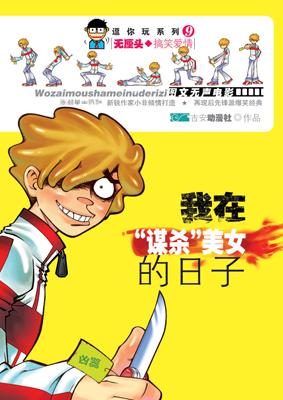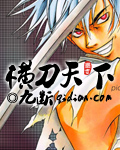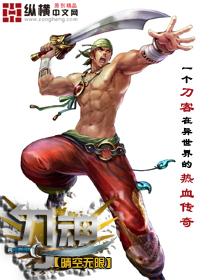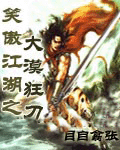大雪满弓刀-第7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轿子里才传来一声叹息,然后他们只听到轿子里的那位贵公子轻声道:“此事和他们无关,放了去吧。”
十几人安静退开一个口子。那些轿夫哪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下也不管什么赏银和轿子了,卸了杠转身就跑,刹那间没了踪影。
那十几人中有人向前一步,缓缓抽出朴刀,语气生硬但态度倒是十分恭敬的道:“请宋四公子下轿。”
其余诸人随之向前踏出一步,同样道:“请宋四公子下轿。”
“你们比我想象中,要来的早。”
轿子里沉默了片刻,然后传出一声苦笑,那位宋四公子,武陵公子的同胞兄弟宋武安,仿佛正在轻轻摇头,缓缓道:“这么说来,我那二哥,终究是反了宋家?”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淡薄的清晨光线下,这片街道里,已经有数十把朴刀被抽出刀鞘。刀身和刀把平分整把刀的长度,被人双手握紧,冷寒的锋面直指这顶轿子。
“请宋四公子下轿。”
又一声催促。轿子里的宋武安嗯了一声,道:“是了,着实是反了。。。。。。”说完这话,宋武安咦了一声,又问道:“你们是上官将军的人,还是谷老大人派来的?”
持刀的这十几人还是没有谁吭声。不过片刻后,有一人皱眉答道:“并无分别。”
“是啊,并无分别。”宋武安轻声一叹。“只怕我那五弟六弟,现在与我也并无分别吧?”
再无人回答,但不回答,便是默认。宋武安也不再说话。所谓的请下轿,不过是验明正身,踏出一步,便是举步黄泉,这点,他不是不明白。
但又能怎样呢?从二哥兰明公子连续三夜未归后,他便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结果。所以他并不吃惊并不慌乱,只是想着,宋家最终还是要散了。不过,他只是觉得,子阳子刚,还太过年轻。
宋家四子,宋武安,挑帘下轿。
清晨京都六部巷前的大街上,多了一具朴刀砍死的尸体。
。。。。。
。。。。。
清晨的军机处。
又是一夜未眠,年纪已经都是古稀左右的三位肱骨老臣熬夜的经历并不算少,然而昨日熬的一夜,仿佛已经熬掉了三位老大人的所有精力,以至于徐老大人和方老大人的形象都有些狼狈不堪,发丝凌乱,眼中布满血丝,犹如刚从天牢大狱里出来似的。
军机处空无一人,本应在此当值的章京小吏不知道何时已经退去,这在位于大内的小屋子里从来未曾有过。也许是陛下不想让不相干的人知道太多事情,这里,只怕几日间都不会有除君臣五人之外的任何一人出入了。
君臣五人?
没错。徐中明、方琦、谷平夏、上官铎。。。。。。总共五人。当然,说不定还会加上一个姓杜家伙,不过那人,现在只是个布衣而已。
谷老大人面容枯槁,常年养生而得的矍铄精神似乎在一夜间消散无踪,使得他现在看起来和那些无所事事在城墙根上晒太阳的老头没什么两样。倒了杯水,尝了一口竟是凉的,盛夏时节,就算凉也凉不到哪里去,然而谷老大人却只觉一股凉气从喉间直入胸膛,忍不住低低咳嗽起来。
徐中明此时的样子比起谷老大人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坐在木凳上紧皱眉头的老大人良久叹了一口气,缓缓道:“武夫,武夫,武夫。。。。。。”翻来覆去只说这两个字,竟是一连说了十几遍。平日里性子耿直的方阁老竟是无言以对,张了半天的口还是说不出哪怕一句话来,只能报以一声悠长的叹息,痛苦的摇了摇头。
“万户百姓啊!”徐中明大人哀叹一声,不再重复那两个字,而是痛心疾首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可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都枯的是谁的骨,不是三军将士的,而是平民百姓的呀!上官铎,武夫,屠夫也!”
“此事。。。。。。是倭寇做的。”方琦老大人面有不忍,吞吐半晌,终于还是稍微提醒了一句。
“倭寇?那他上官铎就睁眼看着倭寇大肆屠戮梅州城的百姓?周边军镇一日二十里,这份军令内阁知道吗,兵部有备案吗?边防调令在哪?虎符在哪?”徐中明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几乎要破口大骂,双手挥舞几乎是要将什么打碎,要将什么扼杀。
“至少,陛下知道。”方琦皱起眉头,然后轻轻道:“陛下要对付宋家,当然先要拿掉玄衣轻骑。”
“可内阁。。。。。。”徐老大人忍不住出口。
“内阁?”谷平夏仿若不胜一杯凉水带来的寒意,微微揉了揉胸口:“内阁运筹帷幄,但决胜千里的,还是那些当兵的。”
徐中明仰起脸,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无力的叹了口气。
“陛下已经责罚过上官,此事内阁不必再提。”谷平夏淡淡开口,一锤定音。首辅发话,徐中明只得和方琦同时颌首。但点过头后,徐中明忍不住又摇头苦笑道:“削职罚俸,这也算得上是责罚?”
谷平夏望了徐中明一眼,没有搭腔,而是沉声道:“今日,梅州城大事可定。宋家没了玄衣轻骑,接下来的事,我们需拿出一个章程来,岁末年关,务必全收宋家。”谷老大人脸色很不好看,但还是强打精神叮嘱吩咐,两位阁老分别点头应是。
沉默了许久,徐中明忽然问道:“谷老,陛下跳过内阁行事,前朝有过多少先例?”
谷平夏老大人眯了眯眼,向徐中明投去深深一瞥,平静道:“前朝。。。。。。前朝没有内阁。”
徐老大人紧锁眉头,再不说话。
此时,军机处外却忽然传来一声呼喊:“首辅大人,上官将军送来一封手札!”听声音是军机处的办事章京,谷平夏老大人喊道:“进来。”
有章京小吏推门而入,躬身行到首辅身前,将一封书信递来,然后再小心翼翼退去,掩上门。
谷平夏看着那封似乎刚刚写好的手札,一时间眉头轻轻皱起,他想不明白这个时候上官铎给自己递什么手札,又会写些什么。在御书房里,这位军方第一人的做法明显已经触怒内阁,他所作所为虽然是受陛下亲领,但此番对内阁而言,印象无论如何都好不到哪里去。
叹了口气,谷平夏启封展信。
信上只写了一句话。
“烟村已无,亭台不在。”
谷平夏尚在国子监时,曾有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年意气风发,首辅大人也曾是名噪一时的风流才子,曾在课堂上写过一首颇有趣味的五言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被时人引为一大风雅趣事,从一到十也不知被人学着翻来覆去写过多少良莠不齐优劣参差的诗文来,那时半个吴国都常常将“烟村四五家”等句子挂在嘴边,竟成一时风尚。
而上官将军的这句烟村四五家,却非同凡响。
没有四五,没有六七。
谷老大人长叹一声,想起了青梅煮酒时节,自己对那个年轻人说过的一句话:朝廷可以帮你杀些人,不露声色。
这些人,看来已经被上官将军杀过了。
今日梅州事毕,那个宋家七子,也该死了。
当真的大事已定,当真的大势已定。
谷平夏老大人一时间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盯着越来越绯红的天空,沉默不语。
本书首发于看书王
第二十二章 宋家在后()
第二十二章宋家在后
离梅州城较近的军镇,当数樊城都尉郭舍麾下的一万步卒,这支被闲置在江南多年未有过战事的步兵也曾是叱咤边关与上官铎将军并肩作战过的主儿。奈何郭舍在边关于上官将军麾下和西烨对峙时曾有畏战避敌贻误军机的罪名,虽然那一仗终究是赢了,但作为主将,罪不可赦。得亏劳苦功高的上官将军多方斡旋,才使得这位其实已经拼掉了大半手下兄弟只是想为营里留个种而命令十八岁以下步卒先行撤后的主将郭舍留了一条命,被贬到了江南道这个在当时看来还无比鸡肋的樊城。
说是都尉,但其实比文职还要不如,江南鱼米之乡,少有战事,且烟雨水乡人心淳朴,连个作奸犯科的歹人都很难找到。他这个樊城都尉除了每天在樊城四周闲逛散心,喝酒打屁之外,竟是什么事儿都没得做,日子一长,连点卯都省了。可随着宋家的崛起,整个樊城的位置也逐渐水涨船高,不但被朝廷看重多加扶持,连那些商人都开始纷纷往樊城靠拢。于是樊城的太守也在不停的改换,原先是京官走马观灯的过渡场所,现今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风水宝地,内阁为此甚至有一年三换太守的记录。但吸引人眼球的,却是另一件事。这些文职们一个一个你来我往换的不亦乐乎,可武职都尉却从来没有变过,始终都挂着“郭舍”这两个不显眼但同时也必将大放异彩的字眼。
那时人们才发现,这位都尉大人,当真是个不显山不露水,闷声吃猪肉的高手。更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都尉大人不知从哪里竟摸出来了一万步卒!难不成是找天上的神仙借的?平日里除了闲逛还是闲逛的都尉郭舍大人一下子赚足了半个吴国官场的目光,连带着那些京都重臣都目瞪口呆,暗道这家伙可真堪养兵将才。也正是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忽然想起来,当年上官将军不惜半折军功保郭舍下放江南的举动,颇为耐人寻味啊。
樊城向北边,是定州城,定州城有上官将军安插的紫衫重甲。定州向南,有樊城和渭城,樊城向西,是渭城。。。。。。明眼人谁看不出来,这分明就是针对宋家所布置的一张巨大网袋。你宋家老老实实还好,若真有什么想法,袋子只怕会瞬间收拢,将渭城变成一座孤城。
梅州事变后,郭舍按兵不动一日,随后便接到了从京都而来的千里鸿将军手札。信上命令他自樊城向梅州靠拢,但速度应持一日二十里,不急不缓。作为将军多年来的心腹,结合着玄衣轻骑开拔梅州的情报,郭舍很轻易就猜到了这里面所包含的莫大涵义。所以他领着自己苦心经营数年的这一万樊城步卒,在玄衣轻骑身后,慢慢逼近梅州,驻扎在平溪镇。
但今日,无法再待下去了。
天将大亮,整军待发,这位在边关浴血厮杀如今身处江南养了多年太平的老将军终于不再沉默下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懂得练兵养兵,但却不懂政治博弈,他只知道,若不是当年上官将军半折军功,他如何能活到今日?上官将军打了胜仗却依然被调回京都任了一个狗屁宣化将军,不升反降,为的不就是自己?那么今日,这欠了许多年的债,总是要还了。
郭舍仰头,明月还挂在西边天空,然而朝阳已然快要喷薄而出。他伸出手,指着梅州城方向,平静道:“全军开拔,奔赴梅州。”
。。。。。
。。。。。
渭城不见日月只有风云,层层叠叠的墨云积压在平日里清朗的天空上,让人感到一股透不过来气的压抑。城中最近接风云的地方,当数宋府内的那座城中山,山上最接近风云的地方,又数那座不起眼的青竹小筑。小筑内最接近风云的人物,当然是宋家说一不二的家主——宋敬涛。然而宋敬涛并无意风云,哪怕厚重的云层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他还是毫不在意,只是站在窗口俯瞰渭城,像是一个迟暮老人,总喜欢唏嘘感叹一般,说不出的萧索落寞。这份情绪若是落在了那些平常人眼中,指不定会惊讶成什么样子。众所周知的宋三爷为人狠厉果决,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会有今天这般黯然?这便是别人猜不到的地方,这便是宋三爷如何手握宋家风雨不惧的地方。
能够进入这间小筑的人并不多,赵铭当然排在第一位。这个御物境的真武高手但凡在宋三爷身边时,就像极了一个温顺听话的管家,丝毫没有任何令人啧啧称奇的真武气概,相反还更加世俗人情了一点。此时的他便是这般样子,轻轻敲门,然后进来再将门掩上,身子不弯但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恭敬,声音平静道:“三爷,东海水师已经走了。”
宋敬涛“嗯”了一声。他原本就是在闭着眼睛的,此时也没有睁开,手扶在窗棂上,宽大的手掌既是是在温热湿润的江南,依旧显现出了纵横干涸的沟壑。
“东海水师既去,樊城郭舍的一万步卒应该也已经上路了。”
宋敬涛再“嗯”一声,还是没有说话。
“五爷领甲字东海路已经到了东边,有四爷铺垫的前路,自然不会出什么意外。大少爷领乙字西海路和窦健所在的丙字南海路停居在南海诸岛国,那里我们经营日久,也不会生什么变故。为三少爷安排的是东移,不过还尚在考虑中。制船工坊核心伙计共三百四十七人已分批秘密送往南海,宋氏各地商行也在销账,短则半月,长则一月,皆可完工。”
宋敬涛睁开眼,淡淡开口道:“冲销账目着实难了些,除了渭城总行账目需销毁部分之外,各处分号都停了吧。”
赵铭点头道:“是。”又道:“东海水师既去,晴山港的动作便轻松许多。大爷已经吩咐下去,家里剩余女眷可由此出海。郭舍的一万步卒离开樊城,城内剩余的玄衣轻骑可从定州撕开一个口子,直扑叶兴,打乱江南水道,为宋家东南两移,赢得足够时间。。。。。。”
赵铭不急不慌,缓缓叙述,然而说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停顿了一下,轻声道:“只是,二爷想要和玄衣轻骑,一起去叶兴。。。。。。”
宋敬涛沉默,半晌叹道:“兰明反了宋家,他作为父亲,自然再无脸面去见列祖列宗。老二这是要拿命,换得祠堂之中,族谱之上,不予除名啊。”想了一想,宋敬涛平静道:“答应他。”
赵铭点头,微微皱眉道:“三爷,梅州那边,是否要再派些人去。”
“已经丢出去两千轻骑,足够让陛下和上官心动,梅州城倭寇也好,朝廷也罢,想吃掉宋家,总是要撑一撑肚子的。”
赵铭道:“属下的意思,是七少爷那边,是否要多加照应。”
宋敬涛一时沉默,然后轻轻叹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