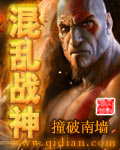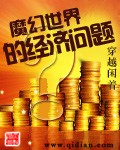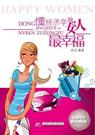���ҵľ���ѧ:����ѧ������������ʲô��-��8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ʸ�ڷ��ϴ�˵�����ơ���ʱ�����Ĵ��������ʽ�ͳɶ�������ȫ�أ�ͨ��ʱ���Ĵ�ʡʡ�����α���Ľ��ܣ��ɶ��ذ¼��Ŷ��³���������ṩ��2ǧ��Ԫ����ʽ𡱣�����������ʽ��һ����ע������ˡ�������Ϣ����
��ʵ������ֻҪ���ס�������Ϣ���нӳɶ����������ģɣÿ��绰�������з��������౾������ȫ�����ˡ�������Ϣ������Ӫ�����ǾͿ������ף�������˭���ʽ�ע�������������Ϣ��������Ҫ����Ҫ�������ܷɶ����ڵĴ�������ת�Ƶ���������Ϣ����ȥ��ֻҪ���ܽ������ɶ����ڵ�����ת�Ƶ���������Ϣ����ȥ����ʹ��������Ϣ����ע���ʽ�����Ǵӡ��ذ¼��š������ģ�Ҳ�����á�������Ϣ������������ܿ컹��ȫ���������ܹ����˼ɵ�����������Ϊ����ȫ�ƿ��š�������Ϣ���ľ�Ӫ���ֲ��ض������Ϣ��
�ڻ����˴���Ļ����£���������Ϣ����ע���ʱ���������˭���оͳ���һ����ȫ�����ɺ���һ����˵��������顣������Ҫ������ֻ�ǣ�����ʲƲ�����˭�����»�ת�á���˭��������Ϊע����Ӣ��ά����Ⱥ���Ĺ�˾�ӣ�����硡�ӣ���ԣ������������̣��������ķ��������ˡ����øù�˾���С�������Ϣ��ȫ����Ȩ����ʵ�����������������Լ���Ϊ��������Ϣ��ȫ���ʱ�������������ߡ�
�ڡ�������Ϣ���������Щ�ɶ������յĹɶ��ӣ�����硡�ӣ���ԣ������������̣��������֮�䣬�����ˡ�������Ϣ����Ȩ��������Щ�м��ԵĹɶ�����һЩ���м��Ե��߹���������ǰ��ݵ��ǡ���·���Ľ�ɫ������һЩ���ö���Ǯ������Щ�ɷݣ��ִ�������Щ�ɷ����ջ���ô��Ǯ�����ˣ�����������˭���ʽ����ˡ�������Ϣ���Ĺ�Ȩ�����dz��˿����ڳ��С�������Ϣ���ɷ��ڼ�ֵù�˾�Ĺ�Ϣ֮�⣬�ڸù�˾��Ȩ�������ϼ�û�еõ�ʲô��Ҳû��ʧȥʲô��
��������Ϣ����˾��ȫ�������Լ����ʽ�ί����Щ��ν�ġ��ɶ������С���Ȩ����������Ǯ��ij����������Լ��Ĺ�Ȩ����������ԭ���������Щ��Ȩ����������������������С���Ȩ�任���Ļ�������ʵ��һ��Ǯ�������ʽ��ض��ã�ֻ��ǩһЩ�����Ȩ������Э�顢�������˾Ϳ����ˡ�
��Ȼ������Ҳ��������Щ�м��߹����ġ���Ȩ�����ߡ��õ�ʵ���Եĺô�����������ij�˲��ظ���͡����롰������Ϣ���Ĺ�Ȩ������������������ݹ�Ȩ��������Ϊ�Լ��IJƲ���������������ͱ��������ʽ������䡰������Ϣ����ע���ʱ����Ӷ�����������ȫ���Լ�֧������˶���������ʽ���Դ��
���ǣ���һЩ���롰������Ϣ����Ȩ�������м��Թɶ�ȴ�õ��˾�ĺô���������Щ��2000��3��9�ա�������Ϣ������ע���ʱ���ʱ���иù�˾��Ȩ���ˡ���һ�조������Ϣ������ע���ʽ���1ǧ��Ԫ����2��476��Ԫ�������ʽ���Դ�ڹ�˾���ʱ������������12λ��Ȼ�˹ɶ��Ĺɷ�����Ӧ�ij��ʶ�������˲�ͬ�̶ȵ����ӡ������Щ�ɶ������涨�ij��ʶ������������������Ϣ���Ĺ�Ȩ����Щ�������������������ʶ���˵�Ȼ������Ӧһ��Ǯ����������������У��ɶ�����ij��ʶ�������870��Ԫ��������ij��ʶ���������40����Ԫ��������������ЩǮ��Դ�ڡ�������Ϣ������Ļ��ۣ�Ҫ������Ϣ��������Ͷ���ʽ�
��������Ӣ��ά����Ⱥ��ע����Ǹ���˾�ӣ�����硡�ӣ���ԣ������������̣�����������Ҳ��ҪͶ��������ע���ʽ�������������ں���Ӻδ��õ�����һ�ʾ��ʽ������������ԭ���ο˻IJŴ������ʣ���������������ʹ�˾�����չ�������˾��Ǯ�Ӻζ�����������ʵ���ϣ�Ҳ��ȫ�����á�������Ϣ����ע���ʽ��������ȫ�����������ɡ�������Ϣ��ͨ��ij����ҵ;�������Ӣ��ά����Ⱥ�������ӣ�����硡�ӣ���ԣ������������̣�����������ν���ɶ�������ע������ù�˾����������ӣ�����硡�ӣ���ԣ������������̣��������������ʽ����չ���������Ϣ������������ؽ�ͬһ���ʽ���Ϊ���۹�Ȩ�������ٻ�ء�������Ϣ�����ϡ�
ֻ���������������ڷ����ϴ�����һϵ�����⣺
���ȣ�������һ�ι�Ȩ�任֮�����ϳ��ϵġ�������Ϣ���������ǣ��ɶ����ڵȹ�˾��Ӧ���ջ�ע��ʱע��������Ͷ�뻪�����ʽ𡣳ɶ����ڵȹ�˾���ʻ������û������һ�ʳ��۹�Ȩ���棬�����ϾͿ��϶���Ʋ����˵��ԡ������������������ʽ�ͬʱ��Ϊ��������Ϣ�������㹻��ע���ʽ𣬺�����ֱ�������ȫ���Լ�֧������˶���������ʽ���Դ��
����ֻ�����ף���������Ϣ������ת���˳ɶ����ڵģɣÿ��绰������������з��������౾����ȫ�����ˡ�������Ϣ������Ӫ����������Ϣ���IJ���״������������κ���֪�������ɶ����ڵĹɶ��̵���ҵ�������ʣ�����Ҳ�Ϳ���֪�����������㹻����ȫ���Լ�֧������˶���������ʽ���Դ�����ԶԸ��ϱ���˵�ĸ����ʽ���Ҫ��
��������һ����ͻ�Գ�һ������Ҫ�ķ������⣺������á�������Ϣ�����ʽ�ע������ˣӣ�����硡�ӣ���ԣ������������̣�������䣬��ô�ù�˾��˭���У����ʽ���Դ������Ӧ���顰������Ϣ�����С�������ӣ�����硡�ӣ���ԣ������������̣����������˺��౾�˻�����ijЩ�ǡ�������Ϣ��ԭ�ɶ��������У�����Щ�˾��ǵ����ˡ�������Ϣ��ԭ�ɶ��ǣ��ɶ����ڵȹ�˾���IJƲ���������һ���ӣ�����硡�ӣ���ԣ������������̣���������ֽ�һ���ѡ�������Ϣ����Ϊ�Լ��IJƲ������ǽ�һ�����ԡ�������Ϣ��ԭ�ɶ��ǵIJƲ���
��ʹ�ڡ�������Ϣ������һϵ�й�Ȩ���֮��������Ϣ���ڷ����ϵ�ԭ�ɶ��ǣ��ɶ����ڵ���ҵ���ջ���ע��ʱע��������Ͷ�뻪�����ʽ𣬵�ֻҪ�˺�����Ϣ����ע���ʽ�ʵ������Դ�ڡ�������Ϣ��������Ӫ�е���������Ȼ�����˶ԡ�������Ϣ��ԭ�ɶ��DzƲ��ĵ��ԡ�����ֻ����Ū��ʵ�ʵĵ����ˡ�
�ϱ��йص�����Ϊ��ָ�ػ�ֻ�����ڶԡ������С���������ʵ�IJ²�����ϣ���ǰ���Ѿ�ָ��������ƾʵ�ݵĵ�����ʵ��������Ĵ����ڵ��óɶ����ڵģɣÿ��绰����������֤���ر��ǡ��Ĵ�������Ϣ�����óɶ����ڵĺ����ʲ������ɣÿ��绰�������ۡ��ɣÿ��绰������������֤�ͣɣÿ��绰�������۶��dzɶ����ڵĺ����ʲ���������Ȼ�������ʲ���ȴ�dzɶ�������������Ļ������������ĺ����ʲ����ߣ��Ǿ��ѹֺ������˵1998��֮��ɶ����ڡ�����̱�����ˡ�
��һϵ�еĵ�����Ϊ�ܹ��óѣ���Ȼ����ΪĻ�����ִ��첢�����ˡ�������Ϣ���͡��Ĵ����ڡ��ĺ��࣬ͬʱ���ƿ��ųɶ����ڵ�ʵ����Ӫ������Ϊ�ɶ�����ԭ���Ĺɷݼ���100�����ڹ��У�������Щ������ΪҲ�ͳ��˶Թ��вƲ��ĵ��ԡ�
��ǰ����ָ������Щ��Ϊ����Ϊ�����ԡ������ܻ�����ijЩ���ɽ���ʿ�����顣���ҹ��ķ����У����Ƶ���Ϊһ�㱻����Ϊ����ռ���������ο˻ĶԺ����ָ��Ҳֻ���ڡ��Ƿ���ռ������ʲ�������Ȼ����ռ���������ȡ����ԡ�������Ҫ��һЩ��
���ǣ�ǡǡ��������ʵ���ʱ������г����õĵط�����������һ����Ϊͨ����������Ϊ�����ԡ������ҹ�����Ĵ���������ʵҲ˵����ֻ�а�����������Ϊ����Ϊ�����ԡ������ܸ����������㹻��ƽ�ijͷ���
�ݡ���һ�ƾ��ձ���2004��12��2�գ�1�汨����2004��11��30�������������в���10������ά���롱�ĸ߲���ʿ����ָ�ر������еĴ�ά����ع�����˾���¾���ϯ�ƺ���������ܻ��������ù�˾ִ�ж��£���������ȡ��˾�ʽ���4800��Ԫ�������������ṩ�IJ���˵������������ȡ������ʽ����Ϊ��ָ������������������2000��11����2003��4���ڼ䣬����һ����ʿ��ı���Թ�9�ŴӴ�ά���������ʻ���ǩ�����ܽ��Ϊ4800����Ԫ��֧Ʊ��
������ѧ�߾ʹ˰�����˵���ҹ����ɶԾ�Ӫ�ߵĴ���Ƿ���Ϊ������ᣬ������Ϊ����ռ���������϶���Ϊ�����ԡ����������������Թ���ķ��ɣ��йط���Ҳ�ܲ�ִ�С�
��۷���Դ�ά�Ĵ�����ɶ����ڰ��γ��������Ķ��ա���۷�������Ļ���ԭ���ǣ��ɷݹ�˾����߾�Ӫ��δ����˾�ɶ���Ȩ��ȡ�߹�˾���TΪ����ȡ����������ǰ����˵�ijɶ����ھ�Ӫ�ߵ���һϵ����Ϊ��������һ��ġ���ȡ����Ϊ��������Ϊ�����������ǰ������������ɶ����ڵľ�Ӫ���ǡ��������йز��š�ȴ�������赭д�ĵ��ԡ����淶��һ�����ɻ���ء�
�����Ҹɲ������������ߵ�����
�ɶ����ھ�Ӫ�����ԡ��ɷ��ƾ�Ӫ��������Թ��вƲ�����������Ϊ��Ҳ��¶�����ǵġ����Ҹɲ������������߶�������һϵ�е��������⡣
����֮���Ի�����ʹ�á����Ҹɲ�������һ�������Ѿ���ʱ���˵����ʣ�����Ϊ������˵���������⣬���������ڵ��������Ĺ�Ա�У����Ҵ��������������ҵ����ҵ��λ���쵼���С�������Щ�ˣ�������ͳ��Ϊ�����Ҹɲ�����
�ɶ����������������д��ɶ���˾����ģ�����д�ɶ������̵���ҵ֮�⣬�����д��ɶ���˾���Ĵ��ʵ�滮Ժ��������ҹ��е�λ�dzɶ��������Ĺɶ���ֻҪ���Dz�ȡ�ж���������˵��κε��Թ��вƲ����ж��������ܳɹ�����������ȴû����ʩ�Լ���Ϊ�ɶ�Ӧ����ʩ��Ȩ�������κ�����ݳɶ����ڵ������������μ�������������Ǹ�����һ�ֲٰ�ġ��Ĵ����ڡ����д��ɶ���˾���μ�������������Ǹ�ת�Ƴɶ���������ġ��Ĵ�������Ϣ��˾������ȫ��������ɺ����Ū�Ŀ��ܡ����������˾��档
�������ǿ��������а�����ǣ��ڡ��Ĵ�������Ϣ����Ȩ����Ĺ����г��ֹ�һЩ�������иù�˾��Ȩ��˽�˹ɶ������ο˻�˵�����е�Ѧ�����ǵ�ʱ���Ĵ��ʵ�滮ԺԺ������������Ѧ����֮�ޣ����������ǵ�ʱ���д��ɶ���˾��������Ӣ��Ķ��ӡ�ǰ������ָ������2000��3��9�ա�������Ϣ���Թ�˾���ʱ������������������ע���ʽ�ʱ����ʱ���иù�˾�ɷݵ���Щ��Ȼ�˹ɶ�ע��ij��ʶ�������˲�ͬ�̶ȵ����ӣ��������ӾͿ���������������������ù�˾��Ȩ֮������Ǯ�����ڳ��ʶ������ӵ����о��ж����ᡣ
�������������ţ���һ���������Ĵ�������Ϣ���Ĺ�ȨŪ���Լ����еĹ����У�����֮����Ҫ���롰12λ��Ȼ��������Ȩ������������ܴ�̶��Ͼ���Ϊ������Щ���ڹ�Ȩ������������һ��Ǯ�������ַ�ʽ�����Ĵ�������Ϣ����һ��������ָ����ǣ��Դ�л���Ǹ����Լ���ijЩ�ô���������������ˣ�����Ҳ�Ϳ�������Ϊʲô�Ǽ����д��ɶ���˾�滮Ժ��������ɶ����Գɶ����ھ�Ӫ�ߵ��Թ��вƲ��ĸ�����Ϊ���Ų��ʣ��������������ϣ�����������Ϊʲô�ڹ��ڼ��ſ�����4�������ʲ����д���˾����ķ����Լ������Ȩ�棬������Ϊ2�ڵĸ�ծ�������Ʋ���
�ɶ����ڵľ�Ӫ���ڵ��Թ��вƲ��������䡰��ҵ���š�ȴ��Ѹ��׳������֮һ������ijЩ������Ա����������֧�֡�
�������Ĵ�ʡ�ط������е�ijЩ��Ա��
ǰ���Ѿ�˵�������౾�˹�Ȼ���ƣ��������Ĵ��������õ�ע���ʽ�����Դ�ǡ�ͨ��ʱ���Ĵ�ʡʡ�����α���Ľ��ܣ��ɶ��ذ¼��Ŷ��³���������ṩ����2ǧ��Ԫ����ʽ�����û�м������ϵ���Ϣ�����ǿ����������˵����������ǡǡ��¶������������ԡ���û��ʱ��ȥ��ϸ�о���λ��ʱ���Ĵ�ʡʡ���α����Ǻ�����Ҳ�������ֹ������˺δ�����ֻ֪��������Ĵ��������Ǻ�����˵��Գɶ����ڹ��вƲ��Ĺ��ߡ�һλʡ����������Ϊ������ϴǮ��˾���ע���ʽ����ǰѵط������Ĺ�Ա����˹��вƲ������ߵ�ͬı��
����ϵ�չ����Ĺ�Ȩ���������У�Ҳͬ��������������Ա��Ԥ�ļ����ο˻��ṩ�����ϣ��ɶ������ʲ��������������ϵ��ҵת�����Ĺɷ�ʱ��������Υ���йط��ɡ�����������İ��³�����ɶ�����ͨѶ�����ţ���˾������2000��5�£������������й�Ȩ��ת�ö��ۣ���ÿ�ɾ��ʲ�ת�ã�����ȴ����Ϊ1999��1��2��31�ա���Щ������Ա��˸�Ԥ����������ú���������Ϳ��˹��вƲ�֮�����л���ͨ���ٿ����й�˾���Ϳ�С����ɣ�
ǰ���Ѿ�˵�����ο˻�����������ٱ������ڵ����⣬���������Ҳ�����Գɶ����ڽ��й����飬�������ֵ���ȴ������֮������û�и��ٱ���һ����ʽ�Ĵ����һ�ͨ��ý��ɢ������֪���Ժη��ġ�û�г��ֹ����ʲ���ʧ�������������ġ����ۡ������������Υ�����С��ɷ��ƾ�Ӫ�������Թ��вƲ��Ѿ����˲��Ҫ���������ĵز��������־�����Ϊ���������ŵ���ʵ�������ġ�������ۡ��������Ժη����Ǻ�����Ϊ��ֵ������ע�⡣������������֪���ˣ�Ϊʲô��Щ��������ҵ��Ӫ���Ӷ���вƲ�����Ϊ���֮����ԭ������Ϊ���������е��й���ʿ��װ��û�����ķ�ʽ�ڶ����ǽ������ݡ�
��ɶ����ڵİ���Ҳ�������ṩ���йء��ɷ��ƾ�Ӫ�����ش��ѵ��
���һЩ����������������Ա�͡�����ѧ�ҡ������ڶԹ�����ҵʵ�С��ɷ��Ƹ��족�͡��ɷݻ���Ӫ�������ƿ���ͨ��˽�˹ɶ��IJιɺͳֹ�����߹�����ҵ�ľ�ӪЧ�ʣ�ʹ���вƲ�����ֵ��ֵ�����������������Ÿ��г�Ϊ���������ơ����ɶ����ڵİ���ȴ�������ǣ�ǡǡ�����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