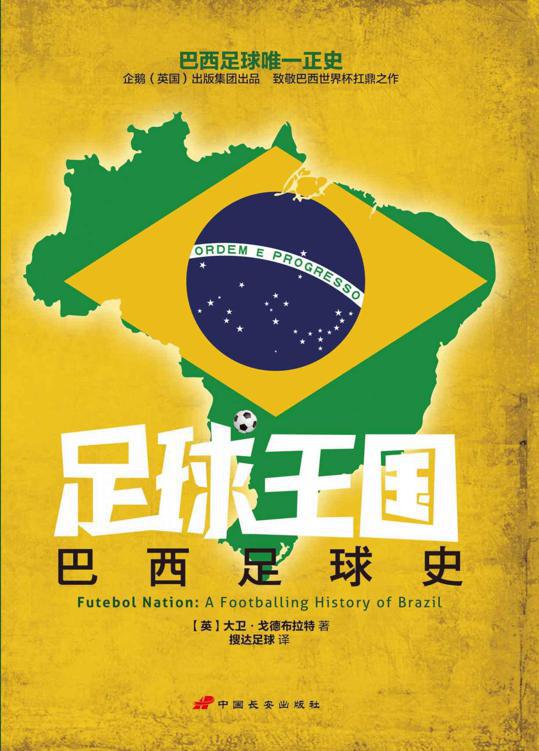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想等自己死后把墓建在这里。由于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诛灭九族。
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气,那就必须造反成功。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祖宗坟地的位置选择非常讲究,它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压在了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不是轻易就会被别人忽悠的。
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这件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朱元璋究竟为何心动?难道正如胡惟庸所言,刘基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朱元璋也明白,凭借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
那么朱元璋究竟在担心什么?那就是刘基的才能,这才是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帝国来说,都是令人头疼的大事。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朱元璋剥夺刘基俸禄的心“动”之举是故意做出来的,做给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态度使得刘基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赴南京城,准备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
刘基重返京城等于是羊入虎口,想要挣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表明心迹,他留京不归。
刘基在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就此放过他。史料记载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情加重。
第13章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3)()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返乡养病。临行之前,他写了一道密文交予刘基,在这篇密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的无情:“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关于他的死,历史在这里打了好几个弯弯绕。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震动帝国上下;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的话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大肆杀戮功臣。
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几段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又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朱元璋还对其他大臣们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
其实在这件事上,胡惟庸极有可能是背了黑锅的。胡惟庸“谋逆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冤案。帝国丞相之死需要给天下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而谋逆是最好的选择。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后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料还在一条一条往他的档案袋里塞。其中胡惟庸下『药』毒死刘基,也就成为其中一条罪状。
胡惟庸接过李善长淮人集团的衣钵,有心将刘基『逼』向绝境。此时的刘基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他不会为了一个老病将死,离开朝堂之人去冒这个险。话说回来,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刘基,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国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一起。
朱元璋除掉刘基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千古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基于死地,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他也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做几个冷漠与怀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不领会皇帝的意思。更何况此时的胡、刘二人势力过分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帝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相互利用,但终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等于是在为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制造舆论,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也算不出来,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的目的就是为了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
如果上面的说法有一个成立,那么刘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
但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抗,这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
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来和一个官场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
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鸡零狗碎的罪名将一个丞相定罪,显然分量还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时间。
朱元璋仿佛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也许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权力机构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第14章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1)()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着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夺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碍。
正面:天降祥瑞引发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顾名思义,“通政”一词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义。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上的下情得以上达。
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
通政使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朱元璋为什么会在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职能就是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呈报于皇帝,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于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
明朝建国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是参考元制而来。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宰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朱元璋做最后的拍板。
当时的情况是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级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让皇帝看见?而这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于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
通政使司的宣告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
胡惟庸内心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这意味着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
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就是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廷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