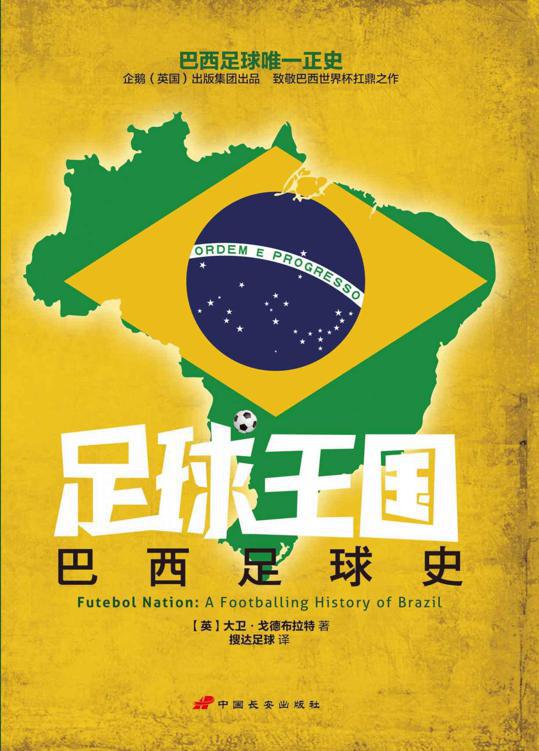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就会落下一个行政不作为的恶名,会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第18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1)()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是李善长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帝国权力中枢的大部分官员还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他们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寻求权力庇护。
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官员们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重判断标准。朱元璋明白,自己要想实现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就要想办法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形成抱团势力。
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也是朱元璋最为不安的地方。
对于朱元璋来说,淮西集团虽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了重创,但是只要他们的带头大哥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一天不会消失。事实也的确如此,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也多是文官集团的人,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最让朱元璋信任的人,莫过于身边那些检校。
检校从建制之初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朱元璋夺权,弹压官员立下过汗马功劳。检校只是个职务名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虽然检校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并入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只会让他们拘束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无法做到任意妄为。
朱元璋要找到清洗大臣的理由,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要向天下人证明一个死人谋反并飞多么难的事,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虽然朝堂上仍有不少淮西集团的官员,可面对栽赃于死人这件事,他们也有口莫辩。
朱元璋要的就是他们有口莫辩的态度,不辨就等于默认。默认就意味着,他们都是胡惟庸的同党,一个也不能少。
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罪『性』质也从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被胡惟庸案牵扯进去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的最后一滴血,正是李善长的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天,注定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上。
一月,李善长定远老家的一段老房子的墙体倒塌,惊吓了这位年近八旬的古稀老人。他只想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子里安度余生,他不忍心惊扰乡里,便给自己曾经的战友汤和写了一封信,要求借三百名士兵修缮房屋。
就在三百名士兵到来的第二天,在他家十五里外的濠塘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如果说朱元璋对这个案子还有一点家丑不愿外扬的顾忌在里面,那么汤和那块落井的石头却砸中了朱元璋的脚。就在汤和借兵给李善长的同时,他的告密信也向京城出发了。有人说汤和太过无情,可是对于权力斗争而言,无情要别人的命,有情却有可能会要了自己的命。毕竟他要年轻许多,还想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他更不想让自己的妻儿也跟他一起上断头台。他在目睹了身边战友们被朱元璋一个一个收拾掉,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么多年的权力斗争,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主人不会将自己豢养的所有猎犬一网打尽,最后肯定会留下一条,用来看家护院、装点门面。当他发现朱元璋的杀气再次出现后,为了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那条看家犬,汤和不得不出卖昔日的鹰奴。
汤和借出的三百名士兵使朱元璋很容易就联想到了刺杀太子的数百名刺客,按照朱元璋以往的脾『性』,他根本不会在这件事上多做周旋,肯定会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里下旨捉拿李善长归案。不过这一次朱元璋欺骗了所有人的直觉,他居然忍住了。刺杀太子的罪名虽然很重,但是并不符合他心中的权力布局。朱元璋没有利用这个事件对胡惟庸案进行收官,是因为这桩刺杀案对他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在其中。
朱元璋决定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他相信李善长还会祭出更加愚蠢的昏招。他已经等了十一年,也不在乎再多等这几个月时间。
李善长就仿佛一个走在布满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他毫无知觉的走过第一个陷阱,却再也逃不过第二个陷阱。
这一年的三月,李善长的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丁斌犯事被判流放,丁夫人在李善长面前痛哭一番,晓之以理、哀之以情,讲述丁斌如何对李善长心存孝敬。或许真是人一老,耳朵根就会变软,丁夫人的痛哭让李善长拉不下这个面子,他第二天给朱元璋上了一封信,‘恳求陛下看在老臣当年的微末之功上,给丁斌一个改过从新的机会吧!’
只可惜朱元璋的耳朵根却不软,他从这封信中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丁斌为突破口。
朱元璋当即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务时,并没有将事情挑明了说。可是詹徽却在朱元璋只言片语的交代中揣摩到了圣意,他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出卖他,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这里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机之巧,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维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之弟,同时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
果然,在继续追查李存义后,他终于供出了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不许,胡惟庸亲自来说,李善长终于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这个‘汝等自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笔,它符合李善长的身份,轻一点说是知情不报,但往深处想就是默许胡惟庸造反,虽然他没有参与,但他已有此心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作案动机。
即使是造反未遂也是重罪,詹徽随即大规模网络罪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跳起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才如梦方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自己,文武百官纷纷跳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太师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赐死,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李善长遭到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
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替李善长说了一句公道话。
王国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这句话就是说,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位极人臣。他没有必要冒险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错。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吗?而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朱元璋看完王国用的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于这个五品郎中,可见他从内心也是认同于这句话的。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很大关系。王国用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致他于死地的刀锋。
不知道白发苍苍李善长临行前是怎样一番心态,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叹。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有着同样的慨叹。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就算生命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他们的心头好。
随后朱元璋又搞了一次权力的再分配。促使权力进行再分配的事件,或者简单地说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最明显的标志。
第19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2)()
李善长和胡惟庸的死并没有让朱元璋停下夺权的脚步,他派出检校,四处收集所谓的谋反证据,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拿出来反复清算。在这种滚雪球似的清算方式下,死了的胡惟庸并依然还在折腾,罪名也在不断地升级中。由最初的“擅权枉法”发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
罪名每升级一次,打击面就扩张一次。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血缘相近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凡是能够牵扯上一星半点关系的,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濂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要受到皇帝的严密关注,就算取得富贵也难以体会到人生的快乐。
宋濂的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了四川夔州。
在胡惟庸死后十二年,帝国再度掀起“蓝玉案”。作为一代名将,开国功臣的蓝玉,受封凉国公,为人桀骜不驯。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朱标就有了亲戚关系。
《明通鉴》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蓝玉身为太子朱标的亲戚,极为关心东宫的权力之争。他曾经提醒朱标要提防燕王朱棣:“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意思是,燕王朱棣不是一般人,收买人心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燕地有天子气象。
朱标却不以为意,淡淡地说“燕王事我甚恭谨”。
蓝玉估计事后连肠子都悔青了,他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太子朱标不要传扬出去,谁知道朱标还是告诉了朱棣。等到太子朱标病死,燕王朱棣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这句话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然还是率『性』而为,一点也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蓝玉在战场上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可是离开战场,蓝玉的表现只能用一介莽夫来形容。他在战争结束的归途中,干了一件颇为让人不耻的事。他用暴力霸占了元主的老婆,结果这位妃子羞愧『自杀』。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不得人心。他的这种做法让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更加放肆起来。
在这之后,蓝玉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在他回到喜峰关口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关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自得。
蓝玉还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当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毫不顾忌结果,竟然堂而皇之地驱逐御史。
诸如此类不靠谱的事件让朱元璋极为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为了警告蓝玉,他把梁字改成了凉字,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
蓝玉征西归来,以为回朝后会得到大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