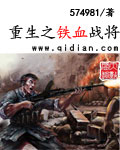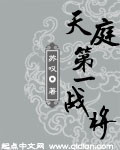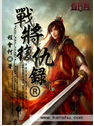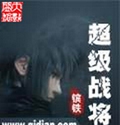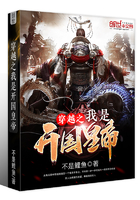开国战将-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狂风暴雨:乌云四合,大雨如注,好像永无止境。说来也怪,下午5点,当向许世友遗体告别仪式结束时,这场暴风雨骤然停息,黑暗中透出一条缝,朗朗的晴空重又在南京城头复现。向来不相信神力的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面前也疑『惑』了,难道冥冥之神在警示着什么?
最后一仗
两只鹧鸪,一雌一雄,栖于高大茂密的相思树上。雄的形体略大,摆动着尾巴,围着雌鸟上下左右跳来跳去。雌鸟温顺娴静,转动着圆脑袋,幸福地应答着,鸣叫着。远处,天空明静,一尘不染。
突然,“嘭”的一声,雄鸟一声惨叫,从树枝上掉下来。雌鸟惊慌地蹿上天空。
又是一声枪响,空中散落了几根羽『毛』,只见雌鸟顽强地拍打着受伤的翅膀,消失在无边的苍穹中。
此时,从密林深处走出一位提着双筒猎枪的老军人。他身上穿着一套整洁的绿军装,脚蹬圆口黑布鞋,一支左轮手枪别在腰间,特制的牛皮带捆住肥胖的身躯,犹如竹篾箍着一只腰鼓形的水桶。他黝黑的脸庞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反差,好像有一部分老了,有一部分年轻了;从一个角度看去臃肿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去更加精悍了;眉宇之间的气韵有时平和,有时凶狠,更多的则是一种在饥渴中即将饮上甘『露』的兴奋。
“首长,打中了!打中了!”警卫员提着一只鹧鸪,兴奋地跑过来。
“妈的,都是病鸟,那一只要住医院了!”老军人连看都不看,大步登上山巅,若有所思地向南遥望。
“醉翁之意不在酒。”将军之意不在亚热带丛林的秀美山水间,也不在山中的飞禽走兽身上;将军的真正目标,是南面那个忘恩负义的邻国。
这是1978年12月中旬,许世友将军奉中央军委命令秘密进入广西南宁。将军一到南宁,便以打猎作掩护,视察和检查参战部队的准备工作。
某高炮阵地,许世友将军走进阴暗『潮』湿的防空工事,目光像一把尺子丈量着工事的长度、高度和宽度。
“你这工事挖得够不够深?”
“报告首长,不够!”
“为什么不够?”
“地下水位太高了。”
“什么?”
“再往下挖就出水了。”
“出水怕什么?”
“水多不好挖。”
“不好挖会死人吗?”
“是,我们继续挖!”
某营指挥所,许世友将军举起望远镜,向四周地形观察。将军命令:“把营长叫来!”
“报告首长!”营长匆匆赶来。
“你看,各连的阵地,敌机能不能发现?”
“能发现。”
“怎么办?”
“进行伪装。”
“那好,严密伪装,不彻底重来。”
“是,不彻底重来!”
“什么叫彻底?”
“和原来的地貌一样。”
“回答得很好。你们干,明天我还要来检查。”
某空军机场,许世友将军的吉普车在机场四周转了一圈,下车便问前来迎接的一位师长:“你们到这里几天了?”
“三天!”
“怎么不做工事?不搞伪装?”
“这是临时发『射』阵地,等计划拟好后就进入基本发『射』阵地,准备那时搞。”
“计划什么时候搞好?”
“大概要两天。”
“两天内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我们马上就搞!”
“对部队要严格要求,不能姑息,累不死人,只会打死人。”
许世友将军检查战备认真严厉,丝毫不马虎,因为他明白:这是自己戎马生涯中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了!
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就曾向『毛』『主席』提出:“如果有仗打,我还想打一仗,然后就休息。”将军好运气!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正巧,打越南这一仗让他撞上了!
1979年2月17日黎明,许世友将军腰别左轮手枪,身披棉大衣,坐在前线指挥部标有作战部署的地图前。突然,他抬起头来,放大嗓门庄重宣布:“时间到——还击开始!”
顷刻间,隆隆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火光像朝霞一样映红了天空,中越边境广西段展现出我军猛烈进攻的壮烈画面:
一组组工兵在敌人的雷场上前仆后继;
一排排坦克吼叫着“隆隆”向前推进;
一群群步兵杀声震天,冲向敌阵;
一辆辆满载官兵和物资的卡车如长龙般向南延伸。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从2月17日开始,至3月16日结束。许世友将军指挥的西线部队攻克谅山,威『逼』河内。然而,班师归来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得最多的却是教训。
第一,30年没打大仗了,很多人对打仗这个东西不适应了。基层干部没有打过仗,有的高级干部也没有打过仗,现在一下子指挥几千人、上万人甚至几万人,要一下子适应战争不容易。
第二,过去我们多是在北方打仗,对于在南方作战,从我自己到下边各级都不熟悉,对于亚热带丛林作战没有经验。10月以后是旱季,5月以后是雨季,我们不熟悉这种气候。对于石砬子山地形认识不足,这种地形易守不易攻,开始时制定对策不力,几天后才总结出有利战法。
第三,是对困难估计不足。打到敌人纵深后,行军无人带路,饿了无人送饭,伤员无人后送。越南也是全民皆兵,大姑娘、老太太都向我们『射』击。
第四,是我们的装备太落后,战士负荷太重。这次作战,战士负荷80斤,有的60斤,既不方便走,也不方便打。过去哪有这么多东西?只背一块薄毯子,顶多二三斤重。我当红军10年没盖过被子,8年抗战也没盖过被子。现在我们一件雨衣淋湿了就有8斤重,太落后了,战士要背子弹,背手榴弹,背干粮,背水壶……太重了!
许世友将军说:“我们是打胜了,可代价也不小,粮食、弹『药』、油料花了不少钱。‘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也伤亡了不少好同志。作为军人,不能怕打仗,也不能怕伤亡。但愿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仗,也是中越两国之间的最后一仗。”
6月中旬的一天,许世友带领前指从南宁返回广州。临行前,将军下令:“我们回去不许通知广东省委,不许搞迎接。谁走漏消息,我找谁!”可是这么大的事,不能不报告中央军委。于是,广东省领导同志知道后,提前赶到火车站迎接。
许世友将军一下火车,便阴起了脸,因为他看到了欢迎的人群。
前来欢迎的省委领导在50年代就曾担任过副总理,无论在资历和地位上都不比许世友差。他满脸是笑,热情地伸出手来。
“妈了x的,谁叫你们欢迎的!”
许世友将军一把握住那只手,猝不及防地用力。
省委领导“哎呀”一声,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将军已经大步而去,钻进了汽车。
归宿前的归宿
在紫金山南麓有一个小小的山坳。山坳里有绿绿的树,清清的水,“叽叽喳喳”悦耳的鸟鸣。一道连绵数里的铁青『色』围墙把这小小的山坳与外界隔成了两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生活氛围。
小小山坳四周有一串明珠般的名园胜地镶嵌在翡翠『色』的山野之间:梅花山、明孝陵、半山亭、中山陵、藏经楼、灵谷寺、美龄宫……这批近年来修葺开放的陵墓、寺院、国民革命纪念地无不向人们尽情地展现雄姿,迎接南来北往的游客,唯独这座小小的山坳始终笼罩在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神秘气氛之中。坚固厚实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大铁门后持枪哨兵的警惕眼神,凡是经过这儿的游客,只能在匆匆路过大门时向神秘的院子投去探奇的一瞥,稍有探头探脑,就会招来一通威严的呵斥:“去去去,有什么可看的?”
小小山坳里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里面的情景很一般,很普通,没有一点奇特之处。解放前这里曾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的别墅兼书房,现在它已经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愿被改造成为“稻香村”了。你看,那扇形的金鱼池里长满了喂猪的饲料——小浮莲;那精美的后花园里种着水稻、山薯和高粱;那小磨石地板的走廊上圈放着山羊和鸡;那花房和苗圃旧址上矗立着臭烘烘的猪圈……只有那幢兼作书房的主楼依然如故,巍峨挺立,依稀可辨当年的豪华、富贵和气派。
这里是风景区里的禁区。
这里是“大观园”里的“稻香村”。
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
这里是许世友将军归宿前的“归宿”。
1980年,许世友将军把家搬进了这座小小的山坳。7年前,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时,这儿一直是他的领地。而这时,根据中央指示,他已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常委。此后,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按照惯例,许世友应该住在北京,在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上班。但他却执意不肯,一定要回南京定居。秘书无法,只得替他向中央领导写了一份要求在南京定居的报告,并提出了两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是身体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准备在南京写回忆录。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例外地批准了将军的这份报告。
轰轰烈烈的一生平静了,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寂寞了,一位不该孤独的人孤独了。在那最辉煌的时期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平静的时期。而这时,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已经冲破禁区,驰进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第5章 许世友:魂归大别山(4)()
在这段时间内,许世友的长子许光常从河南老家来看望父亲。他对许世友的晚年生活是这样叙述的:“我真不理解爸爸过的那种生活。1981年,我和定春(许世友的侄儿)来看他。当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卧室里用一个用罐头自制成的木炭炉炖火锅,里面是萝卜羊肉。我真是大吃一惊,我在部队30年,还没有见过哪个首长用这种东西烧饭吃。我说:‘你不是有炊事员吗?’他说:‘他们不会弄,这样炖起来好吃。在老家,过年、祝寿才吃得上这样的菜呢!’接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件怪事。父亲的腿在长征过雪山时受过『潮』湿,落下病根,每逢天阴下雨就浮肿酸疼。他自己用一个装满热水的塑料袋裹住膝关节,用麻绳绑扎起来,我问他为啥不上医院治治,做做理疗。他说:‘我的法子灵,我们家的人一生不打针、不吃『药』、不进医院。中央领导中,凡是进医院的都会死,凡是不进医院的都死不了!’那天,当我们离开这里准备回家时,想不到爸爸竟叫警卫员扛来一麻袋山薯说:‘你背回去吧,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种的!’我既为难又好笑,我说:‘咱家乡哪缺这个?’他说:‘这里便宜,只要七分钱一斤。’我笑了:‘家里只要三分五一斤呢。’爸爸沉默了,他摆摆手说:‘那就算了!’后来,他还硬让我们带上他自己腌的一罐酸菜。”
许世友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供的将军晚年生活情况是这样的:早晨,打拳或锄草、种菜;上午,看文件、读书;下午,午休起床后乘坐吉普车进山颠一圈。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散步”方式,不坐在车上颠上一颠,浑身就不舒服。接着或打猎或钓鱼……晚上,看电视,主要是看《新闻联播》,其他的电视节目基本不看。他介绍说:“将军晚年嗜酒如命,一天一瓶茅台酒。就是病重时也不断酒,买酒用去了他大部分的薪金。他喝酒是公私分明的。因公宴请的酒,由管理员保管,平时自己喝的酒由他自己买,自己保管。幸亏将军死于烟酒涨价之前,否则他的工资更不够用了。”
没有『主席』台上的赫赫光圈,没有宴会席上的山珍海味,没有文山会海的困扰,也没有前呼后拥的烦恼……应该说,许世友的晚年生活是相当平静的,虽然这期间不停地冒出有关他的各种传言。
平静的生活有时也会卷起不平静的波浪,那是他当年走出这个小小的山坳的时候……
将军临终前半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许世友突然提出要到“临汾旅”去看看部队。27年前,将军曾在这个部队六连七班当过一个月的兵。扛着三颗金星肩章的将军在一个普通的连队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将军下连当兵”的这段历史,至今仍然闪耀着令人神往的光彩。
——我们同战士们无话不谈,成了知心朋友。有的战士把未婚妻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战士们淳朴热情的阶级本质、组织纪律『性』和忘我劳动的精神,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下连当兵的同志。
——战士们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无微不至,有时夜间还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去站岗的时候,班长和战士都不让我们去,经我们再三恳求才答应。但他们总有人悄悄地站在远处,帮我们站岗放哨。夜里,连、排干部和战士怕冻着我们,都来给我们盖被子。
——在休息的时间,年轻的战友团团围着我们,攀着肩,拉着手,欢迎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有的喊:“欢迎老许同志打个拳吧!”
——在我们游泳训练上岸时,战士们围在我们身边,用手『摸』我身上的伤疤,问我是什么时候负的伤,哪个伤疤是哪个敌人打的。当他们问清楚了以后,天真的眼里流『露』出对老辈同志的羡慕和敬爱,心里燃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有一次,爆破试验时,老班长孙承仕主动坐在我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我,而不顾自己安危,防止万一发生危险。
……
将军晚年常常回忆起那一段具有人间温馨的美好时光。金『色』的阳光是那么和煦、温暖,溢满心田。麻雀在屋顶欢跳,青蛙在池塘鸣唱,树枝上挂着八卦图似的蜘蛛网,缕缕银丝,闪闪发亮……
而今天,军营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