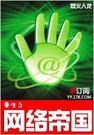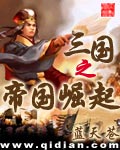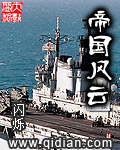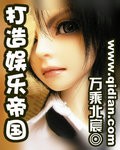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危微精一: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与各种物欲联系,是危险的;道心就是各种伦理道德的准则,是微妙的。只有“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皆人名,多为孟子学生,孟子中有与孟子问答的内容],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吴棫:宋代音韵训诂专家。著有韵补一书,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又名“博学鸿词科”。皇帝特旨开设,由地方官推荐参加。],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社会
明代后期,日本和美洲白银的输入,为中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贵金属通货。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迫于生存压力,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游离出来,努力在商业集镇中寻找新机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商业集镇,其中尤以江南地区为最。
在商品经济之中积累资产的富裕地主、商人、农民,出资供养自己的子弟就学,参与科举考试。这些新兴的地主、商人子弟一旦科举得中,便可在官员集团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官员、士绅的混合阶层不断试图向北京的朝廷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地方上,它们又与当地初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准备应试的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一种联系又是联结官宦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纽带。
相对于传统士大夫对帝国抽象的绝对忠诚而言,江南地区新兴的士绅更留意于本地的利益、风俗以及传统。这些士绅最初由于生活方式、趣味的接近而结成一些文学性的社团,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文学性的社团也可以用于政治意愿的表达。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不见得欣赏江南士人对朝政的非议、批评,但是对文学社团的镇压适得其反,激起了江南士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旧王朝最后的岁月就在镇压、安抚、抗议的交相反复之中渐渐流逝。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在青年时期与上述的运动牵扯甚深。他们往往生于优裕的家庭,后来又经历了朝代更替之间的兴衰。在反思帝国的崩溃时,这些学者的见解,大多来自于江南士绅阶层当时的生活经历。因此之故,对于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言,他们的反思很难说完全恰如其分,但却非常罕见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趣味和意愿。
第85章 守 令()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九守令。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士绅阶级日渐发达。元末明初,江南士绅在内战中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并且支持了朱元璋集团改朝换代的努力。明后期,江南士绅组织的文学、政治团体在朝政上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地方上,士绅向来是宗族利益有效的代言人。士绅往往利用自己免税的特权,帮助族人避税,并以此增加自己在当地的影响。身为候补或者致仕官员集团的一员,士绅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地方事务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万历年间,商业集镇的市民反抗朝廷的增税法令,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之中。顾氏一族是江南典型的士绅家族,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顾炎武关于守令的论述,可以视为江南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之后的反思。
守令以古典的政治语言宣告了近代地方士绅政治的萌发。在商业发达的集镇里,具有商人、地主、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士绅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农民和市民也发现在对抗远方的朝廷时,士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种政治势力一度隐藏在帝国政治的幕后,直到帝国渐渐衰落,才异军突起。晚清时期,在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政治空隙里,士绅政治乘势而起,并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王朝。同一时期,在朝廷影响被排斥的条约口岸,士绅也发现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势力的合流后来推动了晚清的地方自治、立宪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满秩:任职期满],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洊至:接连到来],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十分同情。苏州的织工在抗议活动中杀死了征税官。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地方士绅却表示同情甚至敬佩。抗议活动的首领自首入狱时,士民夹道相送。地方官员受此影响,努力向北京朝廷疏通,赦免抗议活动的首领,以安抚地方士民的情绪。
天启年间,江南士人进一步卷入北京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活动引来了执政宦官的嫉恨。宦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逮捕相关的士人。江南的士民并不了解北京的纷争,但是他们十分同情这些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士人。在执行逮捕命令时,直属宦官的捕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发展为抗议者对捕役的攻击,多名捕役因此丧命。朝廷决定不再宽赦这种近乎叛乱的活动,五名为首者自愿承担责任,以免朝廷借此株连。五人受刑而死后,被江南士绅视为为正义殉难的英雄,其事迹在纪念性的诗文中广为传唱。
宦官失势后,胜利的士人在碑文中将死难者推为反抗宦官专制的英雄。这种论述未免言过其实,地方性的利益、情绪以及政治认同无疑是激发抗议者行动更直接的原因。因为碑文的作者也承认,向来在道德修养上被寄予厚望的官宦、士绅并未比这些出身贫寒的殉难者表现出更多的勇气。
第86章 正 始()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当时,汉末党人的政治影响已经消散,宫廷贵族文化盛行一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杀戮亲曹魏的贵族,并以恐怖政治打击政敌。在司马氏的分化、打击下,曹魏朝廷分化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司马氏一党挟持宫廷,操持军政大权,残酷镇压了曹魏残余贵族的反抗。
经历政局动荡的贵族失去了政治热情。自此之后,贵族对皇室三心二意。士风浮华的背景下,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持久。恢复封建、以宗室镇抚地方的努力首先引发了残酷的帝位争夺战。争战的各方尽力拉拢胡人参战,帝国、贵族以及文明相继在内战中湮灭。在帝国的废墟上,胜利的胡人建立了许多昙花一现的王国。
“五胡乱华”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直至六七个世纪后方才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相信满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终结。在顾炎武看来,文明当下濒临的危机,甚至与一千多年前胡人入袭的黑暗年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明帝殂[魏明帝: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226—239年在位。死时遗诏权臣司马懿与宗族曹爽共同辅政],少帝即位,改元正始[正始:少帝,即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9年],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