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不仅不是对医生的不敬,恰恰是对医生最高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医生这个工种,理论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没有有效性来得重要。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不如他是否敬业、是否有匠心、是不是肯死磕来得重要。
医生的精进这本书里面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有一种病,叫囊肿性纤维化。这种病具体的原理不得而知,但是它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很多分泌物变得非常黏稠,而且没有办法排出体外。请注意,这种病可不是一种能治好的病,因为它属于遗传病。只要你生下来带这个基因,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现在医学也拿它束手无策。
得了这种病会马上死吗?不会,黏稠的分泌物会慢慢堵塞肺部,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只要把分泌物排出来,患者的寿命和没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差不多。
在美国,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医生叫沃里克。他的病人有的已经活到了67岁,而且过去10年里没有一个病人死亡。这也算是一个奇迹。沃里克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招。
第一招,他发明了一种咳嗽的方法,要求病人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再深深地弯下腰去,然后猛然站起来,奋力把胸腔里的分泌物咳出体外。每天数次。
第二招,就是捶背。他在患者的胸腔处画了14个地方,每天找人捶,捶前胸、捶后背。没有人帮忙捶后背怎么办?沃里克发明了一种背心,穿上之后,感觉就像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颠来颠去,捶来捶去,每天两次。
第三招,就是严格执行。他要求患者一生中每天都坚持这样咳嗽和捶背。这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沃里克对患者说:“如果不按我这个方法治,你每天发病的概率是0。5%。但是如果按我这个方式治,概率就会下降到0。05%。”你不要看只有这么一点差距,每天积累,一年积累下来,你的存活概率是83%。但是不用这个方法,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6%。
在长时间段里面进行死磕,这种医疗方法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但是只有在沃里克这种严格的医生手里,才能把它坚持到底。
再比如,有一种常见病叫疝气,得了之后非常痛苦。这种病的机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体内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位置,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弱点、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所以非常疼。治这个病很简单,在外科手术里面算入门级的,手术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种外科手术也有10%~15%的失败率。失败了怎么办?无非就是再挨一刀。对于成熟的外科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就跟补锅差不多。但是,葛文德医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现一家医院,居然把疝气手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首先,失败率低于1%;其次,基本上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最后,它的医疗费用只有其他医院的一半左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翻开底牌一看,简单得不得了。
这家医院除了疝气手术,别的什么病都不治。它一共有12个医生,一年平摊下来,每个医生要做600~800例疝气手术。熟能生巧,一件事情反复做、长期做,当然就成了个中高手。
其他医院的外科大夫什么病都得治,那么他们一辈子遇到的这个病例可能都不如人家一年遇到的多。
这家医院确实做得好,也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很low吗?这家医院的医生跟富士康流水线上装配ipad的工人有什么区别?没有技术含量。那么,医学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是治愈的效果还是人们所期望的智力含量呢?
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怎么当一个好大夫?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就是以上讲的三招:第一,持续地做;第二,系统地做;第三,死磕地做。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
讲了这么多,我就是想破除一下“创新”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智力崇拜。人们总是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必须具备极高的智慧含量。这题得难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而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人,他一拍脑袋,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法把题给解了,这样的人才算是牛人。
就像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很多人就批评她:“这算什么本事?在那么多味中草药里慢慢淘,淘出来一个青蒿素,这是偶然、是侥幸。你看她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说明这个人的科研能力一般,她得诺贝尔奖就是侥幸。”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看着那些生物学博士穿着白大褂,好像很高大上,其实他们天天就是刷试管、配试剂、培养细胞、记录实验数据,错了再重来一遍,没准儿什么时候就能得到一个科研成果。
我们现在给这种科研取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密集型科研”,跟富士康的工人区别不大。但是,你能说他们搞出来的成果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吗?什么是创新?这本身就是创新。
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扩大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届得主是伦琴,他的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x光。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吗?不是,他就是细心。
他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管子可以发出一种具有很高穿透性的光。他很好奇,于是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拿这个东西拍一拍,拿那个东西拍一拍,他发现这个射线可以穿越任何东西的内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了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伦琴得到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他得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射线到底是什么,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x射线。这难道不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吗?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2015年年底,我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搞一次跨年演讲。我跟很多朋友说:“这次跨年演讲只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坚持。我至少要做它20年,从每年12月31日晚上8点半开讲,一直讲到第二年第一天的凌晨一点半,四个小时。也许我讲的东西并不精彩,但是重要的是我会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我这番话说完之后,所有朋友都觉得,这件事肯定能干成。
我自己也预期,也许第一年卖票都很困难,但是做到第三年,卖票的问题就会解决。做到第五年、第八年,没准儿电视转播权都会值一点钱。如果我真的坚持了20年,它一定会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地标,甚至是一个奇迹。
2015年,我也许只是一个傻呵呵的坚持者。如果我真做了20年,做到了203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创新者。
关于创新,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人类就是一窝老鼠,往一个迷宫里一散,每一只老鼠都在夺路狂奔。有三种老鼠,第一种老鼠糊里糊涂的,别人往哪儿走,自己就往哪儿走,这种老鼠跟创新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还有两种老鼠。有一种特别聪明,他们知道怎么能走出迷宫,也总能走对。这种老鼠太少,人类中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才能做得到。
还有一种老鼠,就是笨老鼠,甚至是缺心眼的老鼠。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能出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死胡同呢?于是,他们拼命地拿头撞,没准儿哪一天就真的能撞出来一条道路。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会眷顾那些聪明的老鼠,也会眷顾我们这些笨老鼠。
02创新:是树,也是网
智商越高,社会竞争力就越强?
为什么我对创新和创造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它太神秘。我们一般都认为,创新和创造出于人的大脑活动。大脑很轻,只有1。5千克,而且每个人都有。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脑科学搞得热热闹闹,其实到现在进展还是有限。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叫人类的脑科学还缺乏一个牛顿。什么意思?在牛顿之前,人类的物理世界也是一团糟,直到出现了牛顿,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写下那么几个公式、几条定理,于是万物归位,复杂的物理世界就变成了简单的几个原理。
人类的脑科学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搞清楚。比如,人类的大脑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有人说120亿个,有人说800亿个,还有人说1000亿个。连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搞清楚,更何况那些比较高级的大脑神经活动呢?比如,知觉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更搞不清楚了。创新、创造这种人类大脑最简单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机理?我们依然一片混沌。
但是,人类的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搞不清楚它的内在机理没关系,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灰箱研究法”。就是根据输入和输出总结出一种规律。
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无数科学精英都在搞这套东西。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现象:有的同学就是学什么会什么,就是有创造力,有的同学看起来却是笨笨的。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进化论的原理,把这种优生优育、智商高的人的基因往下传?
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都流行一门学问——优生学。而优生学的底层逻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残忍。现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笨家伙原来应该被饿死的,可是现在饿不死了,侥幸地逃脱了进化论残酷的“自然选择剪刀”。怎么办呢?你本人可以继续活,但是你别生孩子了,把生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聪明人、那些优秀人种吧。这样数代之后,我们人类的整体素质不就提高了吗?这就叫优生学,或者叫“积极的优生学”。
这套原理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惨无人道,就是搞种族歧视,但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纳粹的理论不就是这个吗?德国人的雅利安人种、北欧人种是最优秀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这些地中海人种差得好远,再往东边的斯拉夫人就是垃圾,更不要说什么中国人了,这些人种都不行,最好都淘汰掉。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搞优生学的科学家是相信纳粹主义的,他们是本着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做优生学的事的。只不过,今天在政治上已经不正确了,他们那时候觉得是带着全人类的正义感在研究这门学问。
其中一个人叫刘易斯特曼,这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纳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一生做的事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智商测试。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看成一个灰箱,要搞出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测试,这不就可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吗?
第18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4)()
比如,75分以下,干点粗活就行了;75~85分的人,可以搞技术工种,比如理发师;85分以上的人应该去搞创造性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你的智商一定得是115分、120分以上。特曼一辈子就想搞出这么一个计划,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也是一个商业项目: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长到一定岁数,就到他那儿测一下,拿一个分数,然后参加社会分工。
如果这套方法靠谱,那还了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们今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甄别人,如果智商测试靠谱,那就再也不用进行高考了,大学直接按这个分数录取。大公司招聘也就简单了。
当然,特曼本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做了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漫长的一个社会实验。这个实验从1921年开始一直做到他去世的1956年,前后长达35年。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他先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了16000个儿童做智商测试,其中1500个儿童的智商在151分以上。他帮这帮儿童建立了档案,然后长期跟踪。这些儿童甭管是上学还是入职、是跳槽还是升职,或者发表一篇论文,全部都跟踪记录,一直跟踪到1956年。此时,这些人有的岁数已经挺大了。
他得出三个结果。第一,这帮人的平均创造力并没有优于平常人。第二,这帮人的智力虽然都很高,但是有的人还是混成了我们今天说的loser(失败者)。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甚至还有住精神病院的,这怎么解释?
更要命的一点是,他淘汰的那些儿童当中,反而诞生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也许特曼在长期跟踪的过程中跟这帮小孩建立了感情,或者他也希望这些人做出更好的成就,所以在漫长的35年中,他经常跳出来帮助这些人,帮他们上个好学校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等。
即使这样干涉,实验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特曼临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应该被我们认真地汲取——“看来智商和社会成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直觉是相悖的,一个人智商高,将来的社会竞争力就应该更强。
优生学真的成立吗?
优生优育是不是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我们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来筛选狗,我们希望它跑得快,就真的能造出那种跑得快的狗;我们希望它长得漂亮,它真的就能长得漂亮,每年国际上还搞各种各样的赛狗大赛。
中国人培养金鱼不也是如此吗?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能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这个原理在人类身上就不适用了呢?因为对动物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可是人类能用单一的标准来筛选吗?
比如,我们现在筛选赛马,确实可以把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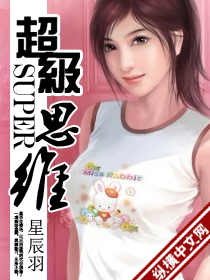



![[猎人]思维不受控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33/33002.jpg)


![[猎人]思维不受控封面](http://www.667book.com/cover/87/8754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