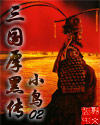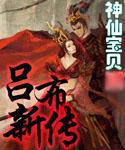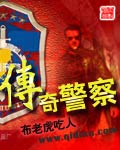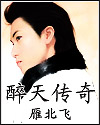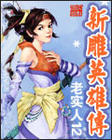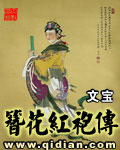���Ӵ�-��3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Ұ������ɢ�ˣ����ϵġ�ʬ�塱��̧����ս�Ϻ��Ĵ��ϣ���Ϊ�����ѱ���˺���ӣ��������ˣ���ȴ����һϢ�д档����ñ�ϵı�ʶ�����е������Ϻ������жϳ����������ʿ����������Ҫ������������λ����ʿ����������һҪι��Щ��ʳ����Ҫ��ҽ�����Ρ�����Ƨ���������ҹ�����Ķ�ȥ��ҽ���أ�ֻ�ð�����������취�����Ǹ��ѵ��촽�ͱ������տ������ܿ��ܻ������Ӳ����������������ѣ���˵���֮���Ǹ�����ʳ������������ͦͦ�ģ���������������ܹ���ʳ�أ�ս�Ϻ����ϰ鰾��һ��С��ϡ�����ÿ���պһ��Ĩ�����ߣ����Ĵ������ƶ��ڶ���ֻ����ϡ��̫�������������ʶ��ⷹ�����ڴ���ת�ƣ�����������ʡ�ս�Ϻ����ֵ�����ڻ��һ��ι����һ����������������������һ���̾ͺ��ˡ�
������������һ�Ե��ϰ�Ӧ����˵������ѽ��һ�����¶ǣ��ܾ���һ�������ǣ��ۼ������̵ĺ��ӣ�������ȥŪ���أ���Ҳ̫Ҫȱ���ˡ���
��������ʮ�����С������үү����˯����ǰ����̬���ѰѺ��ӳ��ѣ�С���ӱ�����̽���������˵�����ۼҵĴ�������С���������̲����𣿡�
�������������ǰ�С������������һ���д��Ϣ����үү������������
���������Ǻ������������ˣ����Ǽ�æ����Ȧ��ȥ���̣��տ��ˣ�ι������ȣ��ָ��������˿ڣ���Щ����ҩ��ֱæ��ۼ�������
���������ڶ��죬������Σ��뿪սׯ���ֵ��������ս�Ϻ��ҵ�����
�����������в���֮���ƣ�˭Ҳ�����ϵ���ʱ���ѹ���֣����������������˱��ꡣ�����������գ�һ�����ղ���ü�ۣ�������ע��������ҹ��ɽ�鱩�������Ӻ��磬ǧ�������̶������ѵ���Ԩ����ӡ��ˮ������ˮ����ˮ���ˮ�����ӡ�塺ӣ�ǧ֧���ɣ�һ��ע�뻴�ӣ���������Թű��ǻ��Ĵ���ϵ�һ�����ӣ������ϹŴ�����ˮʱ���������������ص㣬����ʱ��һǧ��ٶ��꣬����ˮ������û�б�����������Խ��Խ�ң����غ���������˼�������ѡ�����겻�磬������������Ţ�����о��������������벻�������������ѡ�Ŀ�·�����ʣ�����½��������Ϊ�������д�ֻ��������ˮ���ģ�ǰ�������и�ɽ��������̶�����ѵij̶ȣ������ڵ��졣��������;�������������£�����������Ϊ���Ĺ��ߣ����䴬ֻ������ɱ������������Ϊ����֮ʦ�����������д˲���֮�٣�������ˣ���Ժӵ̾��ڣ����ݱ��ͣ�ׯ���٣���Ϊ�����Ͽ���ʵ����ʦ�Ǽ����о����ģ�����Ͷ�ڿ������ն����������ˮ�𣬽����ڵ����أ�����Զ�룬���Ӿ����룬��������ʾ����������Ȩ�����ã������ר�����ȡ���߶���ǰ�ߡ����������϶�Ҫ�Ƴٷ��ĵ�ʱ�䣬Ҳ��ʹ�������ƣ��״̬����ֳ����������ּ�������ۣ���ȴ��ȡ�ö��ĸ���������ģ��������Ǻ���Ҫ�ģ�����ս��ʤ���ľ������ء�������������ʧ�еã���ʱʧȥһ��ʱ�䣬��������������ܰ��������ø����ʱ�䣬���ް���ǰ���ӷ��������µ��������ӣ��Ļ��н����о���һ����˳��
���������ӵ��ϣ�������ð�����գ���������̧�����ˣ�¿�ԣ�������ǰ�ߵ��������ʿ���������մ���Ҳ�������ʿ��
��93�¡���ʦ�ֳ��������µУ�4��������
��ˮ��࣬�ӵ��������ۿ���Ҫ���ڣ������ʿһ����������ˮȥ���ֳ��֣��粢�磬���һ����ǽ����ס����Ű�ĺ�壬����û�������������ɳ����������ҹ��ս��©����ס�ˣ�������ƽ�ˣ������ų��ˣ��ӵ̱�ס�ˣ��������ʿȴ���������࣬��ˮ���ߣ���ɳ��ѹ���˰���ߡ�
����������ˮ��û�˴�ׯ������ǽ����������Ư�������������ߡ������ʬ�壬Ϊ������������ڣ������ʿ�������ڻ��������������˥���߶���û��ˮ���沨������ȥ��
������������������˳�����ת�Ƶ��˰�ȫ�ش���������ʧȥ�˼���ʧȥ������ͱ��죬ʧȥ����ʳ�������伢�ź�֮�������ڶ����Ҳ����ţ�������Ļ�����Щ�ϵġ�С�ĺͲ����ߣ���������Щ�����ٶ��������統����������ǣ���������ר�����������ϸ�㣬������ʳ�������֮�����ľ�ȼü֮����
������������ͣ�ˣ���ˮ���ˣ�������������Ŀ���꣬�������DZϾ��Ѿ��ع��������ʼ�ؽ����������ר���ʦ�������ڰ�����ӭ�����������������������֧���³���ֱ�룬Ѹ�ٵִ�ˮ���ߣ����˺ӱ���ǬϪ���Ǹ����ij��ˡ���ʱ���������ͬ��������˵��Ҫ��ˮ�����������������Ƿ���ֻҡ���������������ӣ�����ʱ����ٳ����ˡ�
��������ȴ˵�������Դӵ�����÷��֮��Ϊ����ɫ������ĺ�ϣ����������뿪�����������������ڽ������ߣ������糯��һ��îʱ�����������ں�����÷��������Ʋ��꣬�������̹��ⱨ�棺�����ʹ�漱�����ɷ�š�ר�㽫����֮һ�����ģ������᧿�Σ��������������������鷢������֮�¡������������ʹ���粻�漱�������漱��ƫƫ�����ʱ��漱���������������ˣ����������ĺ��¡�Ȼ�������������ʹ�漱�����������������룬����ֻ��ʮ���ֲ���Ը���ƿ����е���������������Ϊ֮��ϴװ���������������ù���㣬���������ֹ��˰��ʱ����Ⱥ�����ѵȵò��ͷ��ˡ����ͷ�Ҳ���ܱ�¶�������ܷ�����ֻ�ö�����������������ʹ�ϵ������������������������������ξȵ����顣����������븽ӹ֮�У�������������������ʶ�������ꡢ��˳�������ƴӣ��깱��ࡣ��IJ�˵����˵����������÷�����㹦�Ǿ��أ�û�������ҳϣ������Լ������֣����������ѣ����ܲ��ȡ��ȱ���Ȼ������ҴҰ�ּ������˾���������ʱ�������������ʦ���������ģ���Ҫ�ش���������������������
���������������ǴҴ����£���ȴû�д�����Ϊ�ڳ�������ཫ���У�û�б������������˫ȫ���ˣ��������������ս�ߣ��������˵㻯�̻壬������ԣ��ñ��������¹��������а�ɽ֮������ˮ֮�ƣ���о�����ɥ��������������֮����dz�֮���������������ˣ�ս��ʤ������Ϊ����ʤ�ͻ�����
������������������ʲ�����������Ϣ���̡����������ԽȪ�������ˮ��ֱָ���ġ�
����������š�ר���ʾ����ˮ���������ij��¡�����̽�����棬��������������֮�����ʳ�֮������ģ����ռ��ɿ���ˮ�������ʿ�ű���Ⱥ�鼤�ܣ�����Ħȭ�����˲��ƣ�������ˮ������ˮ֮�������Ѫսһ������һ���ۡ������ר�����˳ϸ�IJ���ﻮ��ʿ���ǻ�����������Χ�İ������ֺ�ļ������࣬���׳��棬������������֧Ԯ���ӭս��������������ӻԾ������������У����ʿ����Ѹ�����ӡ����������������ս��ú�����ң������ݱ��ʱ���п�����ҹ��������뱼�������������ӵ�����������ר�������ʲ����£��������ٶȷ�Ծǧɽ�������ˮ���г�ǧ��֮ң���ֱ���Χ���أ���ʡ�����У��랝��qi��n���أ���ʡ��ɽ�ض�����������ֻΧ��������������Ȟ���Ҫ�������˞��أ���ƻ��ؽ��ֻ�Զ�����ӵľ�������ϸ��д���˹��ǵľ��巽���������ϸ�����ִ�У����а���������ؽ��������£�
��������������ɽ�������ר�㼴�����پ��ã���ʦ���£�ֱȡ�����랝�ء�һ·֮�ϣ���;����������������ɽ��·����ˮ���ţ���鮳��������ж����������н����伲��磬���������������ר����ʵ���������ǰ�ϵ���Ŀ�ĵء�
�������������˻�ɽ��Χ��������֮һ������λ�ò�����Ҫ�����������г�֮�������ϵ�������֣����ڴ���ǧʯ���ϣ�������������������֮���㡣�����ؽ��ֻ�Զ���Ǹ��������ϵľ��ҷ������IJ�֪��Ң��˴���䲻��������������Ů����÷���ڹ��еó�������������������������ұ���Ϊ���ɣ���Ϊ���ϡ���������Ź�ȡ���سǣ�����Ҫ���ֻ�Զ������Ҫ�����֮���иҶ���һ����ë�ߣ��ؾ������£��и��˺��������ߣ���ն���⣡����ǿ�������ܸ�����ô���صĴ��ۣ�ҲҪ����ֻ�Զ��������Ҫ���ġ�
��94�¡���ʦ�ֳ��������µУ�5��������
���ָ�Ӳ���Χ���˞��سǣ��Ը��ְ취���г�ս���ֻ�Զ������֪֮������֪�Լ�Զ�Ƿ��֮���֣�ʼ�ձճǹ��أ��������������������������ֻҪ�����³dzأ����ھ���Ͳ��ᱻ��������Ϊ�����е�����ʳ��
��������Χ�ǵĵ��������ͣ�����Ԫ˧��ָ��������ʿ�䣬���㷹��֮���Խ�����أ������ǵĸ�������������ʱ����Ź�����һ��Ԫ˧�ȫ����ʿ�����л��ֻ�Զ�����ߣ�����ʮ��ߪ������������ɱ���ֻ�Զ�ߣ�ս������������Ϸ�ԣ����ο�����սǰ�����أ���ʿ�Ǹ���ԾԾ���ԡ�������ҹ��ʱ�����ڻ���Ũ�̹����������죬�յ���������������硣��֪��ʱ�����˶��Ϸ磬Խ��Խ�������������������ƣ���������ȼ�յ���������žž���죬���سDZ����һƬ�����Ź���Ũ�̣����ϴ������Ͼ���Ȼ������������������������������ټ��Ğ��س��ó���һ���ݺ�����Ű������ӵ�ּ�⣬ָ�Ӳ��ӳ��Ż��ң����Ż��dzǣ�����ٵع�ռ�˞��سǣ���Χ�����ø��������ֻ�Զ��
������������յ��dz��ڱ߾����ͼ��ĵ��ȣ��Ż����˳���һ������������趡�ԭ�����ֻ�Զ����̰�ƣ����Һ�ɫ���������Ů��ͮ�ƣ������ף�����Ϊ����һ�����ֻ�Զ����ռͮ��Ϊ檣�ͮ�Ʋ��ӣ�Ͷ���Ծ����ֻ�Զ������ȫ�ҡ�����趽����ӳ������������������������ӵ������Ϊ������������˞��سǡ������֡����ֻ�Զ��ս���Ƿ��ָ�ӵģ���ȴ�����ӵ��ݵ����ٵĴ��ۻ�ȡ��ʤ���ľ��Ķ��ǵ�ϲ�硣
�������������������ų���ʿ����ɽ��ˮ����ҹ��ͣ�ر������ģ���δ�����ʺӣ���Ϥ�������ָ���ű����������¹�ռ���������ء�������ȷ�ǵ���֮���������϶���������µ�Ŀ�����ջٞ��ص����֣����˲�����������һ�Ѽ�����룬����ȱ����ʳ������ô�о���ս�����ٺ��Գ�ǿ����˱���������£����ڷ�ŵ�ǰ�߸ϵ����أ�ӭͷ����������������أ���ס���֣�������ʧ������Ҳ������ˡ�����������ⴿϵ�����õ�Ը��������ʵ�ʵij������룡�������Ѯ�����ϣ�������ʿ��ʹ���˲���˫�ᣬҲ�Ѹϵ������ǰ�ߡ����������Ĺ��������ƣ���Ϊ��ʦ����������о����������죬���ٱ�����ţ��ǽ�������������������븽ӹ��������ǰ����������Ԯ�����伲�������ǡ���ʵǡǡ�෴��һ·֮�ϣ���·�ٻ��ˣ���������ˣ���ֻ�����ˣ����ջر��ˣ�ֻ������ͣͣ������һ�����Ǽ��գ����Ҹ���·���������ѡ�������Խ���ļ����ǣ�����Խ�����ǰ��������������ð���ɣ��������ף���Уξ����ʿ�䣬����գ�Ū�þ�����ɢ����Թ���ڡ�������������£�����ǰ�����Ե��������أ�������ǿ�����ѹ��Ū��ȫ����ʿ�Բ��÷���˯���þ�������ƣ�ڱ����������ģ���ʿ��ƣ�ˣ�ս�������ˣ�ʿ�������ˣ��������ӵ�ʿ���������࣬Ū�������ñ����Ƶij���˾�������罹ͷ�ö���������ϣ��ȸ�������ʱ���������ѱ��٣��dzؼ�����Ϊ���棬�����ר������֮��������Ѳ�֪ȥ������������գ���ǰ�������ƹ��������������ڣ�һ�������紵������ʱ������ɢ�ˡ�
������������������Dz��ƣ���Ǩ�����ϸԣ���ʡDZɽ�ؾ��ڣ������������������еľ��������Ű������������³�ʱ�������ɲ�������֮����֮��һ���������������Ǹ��µ��ٶ�ֱȡ��֮���أ������ʡ��ɽ�ؾ��ڣ��������˳�֮����Ҫ�壬����Ϊ���ұ���֮�ء��������ű���һ�������������ʦ�������ң�������˾�����ʱ������Ӵ���һ·ӭ����ʦ��ʹ�����������γɼй�֮�ƣ����������ȷ��������Ҫս����������ء�Ȼ������֮����˾����ͷ�ʾ���;���棬������ʿ��ƣ�������ظ�������ʱ�����������ȥ�������ٴ��˿ա���˾��֪̽���ȷ�ѻع������ʦ�س���
��95�¡������ʦ�����˵����1��������
�ڶ�ʮ�������ʦ���˵��
��������ȴ˵����һ�ˣ��������������벮������֮����֮һ��ͦ�������������س�Χ��ˮй��ͨ����Ͱһ�㡣����������֮�ѳ�������������ӹ��
������������ճǹ��أ�����Ӧս����ӹ������ȼ���Ŷ�������Ұ�ģ�������������������سǽ����ֵܶ��ˣ������ҵ�ʤ������ִ����֮���٣��������ر�ս�������ʱ����ʵ�֣�������ȴ����ΪȻ�����ĵؽ���˵�����ҽ�������֮�������ȡʤ����֮�ڣ�������������Ϊ�����������Գ�����ʤ��Ӧ�ڳDz��ھ�������ڳ�֮���ѳɸߵ̣��Է��������֡�ʱ��Խ��Խ�ã��о��������ѣ���Ȼ��������
��������һ���Լ�����ӹ���������������ڵ�����ս����˵���������η�������绢�ڣ�b��n��������㵨�ӣ������ս���ҷ�ֻ�����سǣ����Լ��������㣬�����֮��ȨΪĿ�ģ��������������������
��������������ֵ���������ֻƾ���£����аܱ���������أ��������ѻ�ʯ�������������졣��
����������ӹ���ֳ���������ԡ����¡��������ѻ�ʯ���������ܸд̶���ʮ�ֽ��⣬�߷�˵�������ҷ����£�ֻ�Dz����Ϊ��С����ı�������֮�����ˣ���
��������������ʱ�������⽫�ֵ�Ҫ�����������ڶ���һ����������ӹ����Ϊ��֮��ͳ���壬ȴ�ѹ�Ͷ�У���Ϊ��֮�߹��������ѳ��������������壬������������ʹ���������ʶ���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