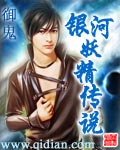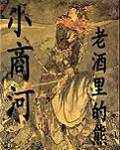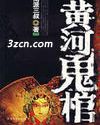细沙河-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简介:细沙河向哪边流啊?春秋桥什么人修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坐车压了一趟沟?细沙河向东流啊。春秋桥是秦举人修啊。张果老骑驴桥上走,康熙爷坐龙辇压了一趟沟。……
://141423
第1章 前言()
列位看官,文勋新作《细沙河》已经完成,正文之前,说几句话,发发感慨,大家忍一分钟,我这书也算有个前言。
新作可能又让一些人失望了,因为又是三无作品:无玄幻、无穿越、无总裁。但是文勋负责任的告诉您,读一下,不会让您后悔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认为的,况且,我得夸我的瓜啊)。做了半生光荣的人民教师,这可是个光辉的职业,时间紧的按秒计算,于是就拿出我们经常教育学生的话来鞭策自己,“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
对学生说了这么多年,自己差一点就信了。于是就开始挤啊。事实告诉我,没挤出水来,可能因为海绵不吃草。那只好朝美好的夜晚使劲了,这些年来,只能在晚上爬格子。有时候爬的整晚失眠,一闭上眼睛,大脑成了大舞台,主角、配角都开始粉墨登场。还好,十几年过去了,海绵不负有心人,终于写出了一部《仁宣之治》,上部就是你们看到的《大明监国皇帝》了。谁知这笔停不下来了,于是乎趁热打铁,写了这部现代小说《细沙河》。这部书再现了六零后这一代人在苦乐的环境中成长,奋斗不息(看官莫笑,起码在下是这样认为的)的故事,主人公的悲喜伤愁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飘摇在细沙河的滚滚波涛中。贫穷与富有、悲苦与欢乐、伦理与人性、传统与摩登交织组成了几十年细沙河的现实版交响乐。
文勋再弱弱地说一句,文勋老矣,没有各位看官和大神们的脑洞,只能是先写完,再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所以我停了《大明监国皇帝》的校对,先把《细沙河》更完再说,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文勋也有足够的抗压力,有板砖尽管向我砸吧,谨受教。不再废话了,感谢各位激情支持。
本文故事纯属虚构,请看官切勿对号入座,如有相似或相同经历,实属巧合。
第2章 大秦庄()
细沙河向哪边流啊?
春秋桥什么人修啊?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坐车压了一趟沟?
细沙河向东流啊。
春秋桥是秦举人修啊。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康熙爷坐龙辇压了一趟沟。
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在高声地唱着,两男一女混杂的声音,像是梆子调,又像是大鼓调,还像是秧歌调,确切地说,是这三种调的组合,这是细沙河两岸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调。几个孩子边唱边向细沙河走去……
先说这细沙河,是北河省数得上的河流,它从大秦庄西南角的几座连起来的小山深处吼叫着、撕扯着奔涌而出,奔出峡谷后,到了大秦庄这片开阔平坦处,似乎没有了力气,没有了脾气,变得温顺了。她绕过大秦庄向东两公里后又向北折去,流经公社所在地,这个公社由此得名,叫细沙河公社。在公社的北面,细沙河被几座山拦住,又折向东方,流经原陵县城,而后沿途收拢大大小小十几条河流,继续向东,水量大增,因地势平缓,波澜不惊,流经平德市政府所在地。
这细沙河有一个绝妙之处,河床坚实,因此不带泥沙,旱季时,两岸是细细的沙滩,就像海边浴场,人们就叫它细沙河,不知道叫了多少年了。这细沙河流出平德市境外,便专门喜欢走丘陵山地,奔腾咆哮,向东汇入大北河入海。大秦庄在河北岸鼓凸着,就像秦秋荣媳妇倒撅着的大屁股。细沙河环绕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恰恰像一个兜裆布,把大秦庄朝阳的一面都包了起来。河上有一座已经破损的小桥横跨南北,有一个不俗不雅的名字,春秋桥。年代已经无法考证,它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到了汛期,政府就把它封了,人们还得用船进出大秦庄。
细沙河流域虽然地处北方,但由于全年降水量不大,冬天里大雪也不常见,而且第一场雪都很晚,往往都是在小雪和大雪这两个节气时,飘几个雪花,也就算应了时令。今年已经过了小寒了才下雪,但是让人惊喜的是,第一场雪一下就是三天,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这三个唱歌孩子就是大智、根生,那个女孩子叫花丽。他们来到细沙河的冰面上,细沙河大镜子似的冰面已经不见了踪影。放眼望去,莽莽苍苍,天地之间、山河、原野都成了混沌不清的银白色世界。天晴了,太阳已经偏西了,虽然没有风,可俗话说的好,“下雪时暖、化雪时寒”。冰面上已经是孩子们的世界了,有的在滑冰车,有的在堆雪人,有的把冰上的雪扫净一块,弹玻璃球、打冰嘎(陀螺)。孩子们的嘴里哈着热气,拖着鼻涕,有的鼻涕流了很长,他就使劲地吸一下,有时这鼻涕很听话地缩了回去,有时却倔强的拖着,于是孩子们就用那打着补丁的油晃晃的袖子使劲地一擦,似乎是下意识的动作,其它的动作一点也不受影响。
根生和大智去滑冰,花丽去堆雪人,大智和根生去滑冰比赛,滑出去很远了,听见花丽在喊,秦秋智回头看了一下,赶紧往回滑。花丽是秋智和根生的好伙伴,三个人在同年级,她妈妈原来是秋智班的老师,公办老师,现在随那个大班升级了。小丽爸爸是镇上机器设备厂食堂的大师傅,掌勺的,她生下来就是吃红本的(城镇或非农业户口),每个月都有细粮(面粉、大米和油类),爸爸的饭盒从来不空着回来,饮食那是村上一流的。平常又勤洗脸、勤刷牙,衣服又没有补丁,干干净净的,和其他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往那里一站,清清爽爽的。
秋智走了过去,花丽说:“秦秋智,你五哥在那边摆手呢”。是大智的二哥,也叫五哥,是按秋智爷爷的孙子排行。老秦家起名字从不含糊,这也是其他家族羡慕的。也不知道上一辈怎么起的名字,秋智爸爸弟兄四个,按朔望晦暝排字,爸爸是老二,叫秦德望,老大秦德朔没了十多年了,三叔年轻时闯关东,就没有了音信,老叔的名字改成了这个“明”字。接下来是秋字辈,名字都是秦德福起的。秦德朔家里有两个儿子,老大秦秋廉,排行也是老大,是大队书记,老二秦秋洁,过继给北梁的三叔秦德寿了,排行老七。德望家有五个小子,两个丫头,按仁、义、礼、智、信排下来,大智是老四,还有两个姐姐。女孩子是不专门排辈分的,为了方便,也占了秋字,大姐秋霞,二姐秋华。老叔家的,按荣、昌、富、贵起名,结果只有三个小子,就让小女儿占了贵字,改成“桂”。秋智二哥排行老五,秋智排老九,大家都叫秋智老九,但是在自己家里都按自己的排。
秋智知道,秋义如果没有重要事不会来找他,马上对他俩说:“是我二哥,我过去一下。”根生也过来了,嘟哝了一句:“不知道你五哥又干啥,装神弄鬼地,有啥事不能过来说啊!”秋智没理他,跑到槐树林子里。秋义棉袄外面套着一件公安蓝的人民装,左面带着一个红色的***像章,旁边插着一支钢笔,这是当下干部们的装束。他瘦高个,又长又重的眉毛下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眼皮黏连着,看不出是几层眼皮,他家弟兄几个长得很像,尤其是脸型,清一色的国字脸,秋智长得尤其像他二哥。他在雪地里站着,搓着耳朵跺着脚,看秋智过来,秋义把着自行车,说:“有人来抓根生他爸,你先别告诉根生,自己儿个去他家告诉一声。记住,谁也不能告诉,家里人也不行,哥上班了,你快去。你说像章他就懂了。冰车让根生他们拿着,在根生家出来后,再去队部告诉根生爷爷去,你办完事就直接回家吧。”大智看二哥这么着急,知道事不小,也顾不上去拿冰车,也不管根生在后面的喊声,撒腿就跑回大秦庄。
第3章 何平的像章()
大秦庄是这个公社户数最多的大队,有两百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土坯墙、黄麦草顶的房子,很不规律地排列了很长、很宽。村里有一个大大的水井,一年四季都是满的,人称满井,就在地面上流出来,形成一条小溪,把大秦庄隔断成南北。这条小溪冬天也不结冰,自然就成了全庄的水源。河北面是起伏的山梁,有近百户房子错落无序地建在上面,庄上人称北梁。把小溪南面习惯称为南地,大智、根生和花丽都住在南地,靠近细沙河。这个大队还有几个生产队在二里地以外,村名叫芦花赤,大秦庄大队部就设在这里。虽然叫大秦庄,可也有很多别的大姓,也没有人统计过最大的家族是哪个。不过,秦姓户门确实不小,而且在整个细沙河公社很有名气,都说这秦举人就是秦家的先祖,还有一点,用秦家人自己的话说,每一辈都有一个读大书的人。单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现在老一辈占德字,下一辈是秋字,接下来是立字、齐字辈,这也着实让这个家族引以为荣,也让庄上的其他姓氏羡慕不已,尤其是何家。
何家也是这个庄的大姓,但何家大多数没读过几天书。队长何平在他爸何碾子督促下进了扫盲班,念了几天书,总算没当睁眼瞎。根生家他常来常往,这是三间房子,黄麦草屋顶,在西面又接出一间,人们都叫这偏厦。不要小看这偏厦,这也是条件不错的家庭才有,这么大的大秦庄没有几家有的,大智老叔德明家也有,他们继承了大智爷爷的老院子。何平家还有两间东厢房,西南角依次排列是厕所、猪圈和鸡窝,周遭是一片花墙子。一进院就知道,这是一个殷实人家。大智跑进去,搅得鸡鸭乱叫,那个大黄狗跑过来,友好地蹭了几下,太熟悉了,也不咬。他看到了糊纸窗户上的玻璃镜,有一双眼睛在往外看,他也不打招呼,直接就冲了进去。一家人都在家,准备吃饭了,就等孩子回来呢。这时是猫冬时节,家家户户都吃两顿饭。根生爸何平一家人看秋智冲了进来,这大冷天,脸上竟然有汗。
何平以为根生出事了,腿都软了。秋智就想让他出来说,他说:“你这孩子,啥事儿,快说,急死我们了。根生呢?”
秋智已喘匀了气,说:“快跑,有人来抓你,像章。”这没头没脑的话,家里人听得一头雾水,何平心里明白。
前两天生产队的马配种,从七队借来的种马,马太烈,四五个人也摆弄不好。何平心疼老爷子,自己带了几个人,总算完事了,发现戴在胸前的***像章没了,何平让大伙儿找,瓷像章已经被马踩得粉碎。大伙儿都挺惋惜,瓷像章确实好看,也不好买。何平想拿起来,捡了半天也凑不全,随手都甩了,说:“碎就碎吧,家里还有,这马总算配种了,瞎了一个像章也值了。”当时有好几个人,庄上当了多年的贫下中农代表耿志也在。何碾子还拉了何平几下。何平也意识到话说错了,赶忙解释一句,“玩笑话,都别当真啊。”大家也都没放在心上,一笑了之。
秦秋智说像章时,根生妈发现他胸前的像章好像换了,挪动着短粗身子,睁大那个总也睁不大的眼睛,仔细地看了一下像章,确认不是那个白瓷的像章,知道出事了。她宽大的肥脸变得灰白,耸了几下粗重的短眉,着急地说:“他爸,孩子来告诉了,肯定有音儿。你快出去躲一下,先上他姥家呆两天,然后再说。这风一过,也就没事了。”
何平摇摇头说:“一定是耿志告的,他们老耿家把耿全的死都算在我身上了。他妈,你放心吧,形势变了,咱们不用怕了。现在‘四人帮’倒台了,不能乱抓乱斗了。”不管家里人咋劝,就是不走。
过了几分钟,堂弟何六儿急匆匆地来了,说:“二哥,刚才来了四个人,去队部找你,是耿志领着,准没好事,你快躲躲。我得快走了,要不知道是我报的信了。”一句话提醒了秋智,他们看到秋智在,不也得怀疑啊。看何平就是不走,秦秋智也不管了,自己走了出去。想去告诉何碾子,快到队部了,他看到有几个骑洋车子的人朝根生家走去,这也太快了。秋智一看完了,根生爸这还能跑掉!这时大智看见二哥迎了上去,不知道和这些人说了啥,这几个人调转方向,朝大智家走去。大智不管这些,跑去队部饲养处找何碾子。
何碾子原来是队长,由于年纪大了,传给了儿子,何碾子自己做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何碾子上几代人都没念过书,他妈妈怀他的时候,都已经大月了,还去推碾子碾米,谁知就生在碾台了,干脆直接起名叫碾子,长大后当了大名,何碾子。他也和老辈的一样,一天书也没念过,可是他却识文断字。解放前他给大王庄王财主家做功夫,主要是碾米推磨,磨坊紧挨着他们家的私塾,他就学会了许多字,也背会了《三字经》、《千字文》等,后来自己也经常借东家的书看。解放后走社会,他有文化,当了队长。他老伴早死了,老爷子专门饲养生产队的牲口,工分还是最高的,一天工分十二分。生产队里有一挂大马车,至少要配备三匹骡马,条件好的要四匹,一匹驾辕,另外几匹作稍马。还得有牛、有驴,种地、收庄稼时使用。老爷子爱讲笑话、故事,据说还会阴阳八卦。他的小孙子根生经常睡在他这里,有时还有根生最好的小伙伴大智也到这里来听爷爷讲故事,有时也听他们大人在这队部谈天说地。大智记得有一次和根生到队部去玩,何碾子和几个人在聊天。那天大智和根生在旁边叠纸楄楫(piaji一种游戏,应该是象声词,打在地上啪叽一声)。听何碾子说看到了“扫帚星”,发着强光扫向“勺子星”(北斗星),炕上的几个人就开始议论,国家要出大事。何碾子今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年不比往年。大伙儿都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今年是一九七六年,确是不平凡的一年,接二连三的大事让这宁谧的山村着实错愕了好一阵子,逐渐地,人们不像开始那样,已经麻木了。大智听到何碾子说扫帚星后,连着几个晚上以撒尿为名偷着出去往北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