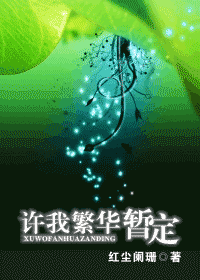许我天荒-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两种,都不是我想要的,前者我太卑微,后者我不舍。
天亮时分,长时间保持着仰靠的姿势一动不动的后果是,全身肌肉僵硬。很是扭动了一番,让血液循环后才勉强站起来,因为还早,所以梳洗并不着急,悠悠转转的,昨晚亏待了自个肚子,那早上不想再亏待,煎了两个荷包蛋外加一杯热牛奶,充分补充营养。
生命是自己的,且行且珍惜,适用在我身上。只要一日时间未到,那就都得好好的过着这日子,等肚子暖融胃畅饱舒服后,才收拾着东西准备出门。射击馆那边昨天是上的白班,今天就是晚班,我打算乘着空余时,去旅行社走一趟,看看有没有零散的活接。
做地陪导游,往往有时候会遇上土豪,等不了凑团就单独聘请导游做向导,这种的收费也相对高一些,毕竟本是面向大众改为了专门一对一服务模式。
可当我拉开院门时,血液凝冻住,为那坐在门前两阶台阶上孤凉的背影。他没有走!天已是严冬,外面气温极低,呵一口气都是白雾,他竟就这么坐了一夜。
眼眶泛酸,定定地看着那似僵化的身背。
他没有回头,以来自极遥远的声音缓缓道:“苏敏,我错了,我不该在那时为了目的接近你,我不该在明知你单纯时还利用你娶你,我不该在娶你之后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你,我不该在心一步步沦陷后还逃避,我不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错当逼迫离婚选择拒绝,我不该在半年前发现你后想着步步为营筹谋将你带回身边。”
一连几个不该,细数了从相识到这刻的过往,我钝钝地想,那许多不该里,其实也有着我对他的纵容,因为我是那么的爱他。
顿了两秒后,他又艰涩开口:“如果我在最初的时候就用心对你,如果我在婚后愿意对你坦白,如果你父亲身故之前我在你身旁,如果半年前我一发现你就赶过来,是否……我还有机会?或者现在,我想问,你还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瞬间,视线模糊,热泪盈眶。
这个背着身不敢回头,低声哀求给他机会的男人,还是我的子杰吗?我怎么就将他逼到如此境地了?极力忍住不要抽噎,哪怕脸上泪痕再肆意纵流。
咬了咬唇,轻声,又足以能让他听到的,“子杰,我就像一块你身上的顽疤,让你难以愈合。总想修复,但却抹不去痕迹。其实你尽管过你的生活,依着原来的轨迹行走,我这疤,虽然看起来不那么好看,会很显眼。但你要知道,再把我晾一晾,我就会褪去的。你也。。。。。。总会痊愈的。”
这番话适用于今后任何时候,包括将来我可能闭眼之时。
眼下的身影缓缓低下了头,将脸埋在了拱起的膝间,接而,清晰地看到他的双肩开始颤动,以着某种特殊的频率。我心如被刀挖般揪心裂骨的疼,甚至凝目的眼都开始充血了。
近似呜咽的声音飘来:“可是你这块顽疤长在了心上,你要我怎么痊愈?”
脑中的弦绷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将我击得粉碎,所有的努力都成了白费,我无法看着这样的子杰而再无动于衷。缓缓弯下腰,颤着双手从他身后穿过绕到他身前,将他紧紧圈住,脸贴紧在他背上,良久,我说:“那么,就不要痊愈了吧。”
偌大的世界,数十亿的人,偏偏让我碰到了他,在我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在我无知过往的岁月里,在无数个情深不寿的日子里,我怎么放得下?要如何放得下?
曾经我把怀中的这个男人比作南墙,别人是不撞南墙心不死,我是撞了又撞,撞到头破血流,还擦擦血又往前走了好久。而今,不但自己疼,南墙也疼了,我终于是求仁得仁,等来了他的转身,却在尝尽悲苦之后。
怀中的身体,颤动的越加厉害,听到他以不太确定的声音在问:“苏敏,你是愿意给我机会了吗?”我哭着笑着答:“嗯,我愿意。”泪滑落在他肩背,渗进衣料中,沾湿了一大片。
这天,我没有再出门,因为在将子杰让进门后,他就以疯狂的姿态将我牢牢锁在怀中,半刻没等撕扯开彼此的衣服,他的唇吞没了我的呼吸,唇是冷的,吻却是滚烫的,他像是异域的火焰,逐渐焚烧我的身体。直到进入的那刻,我都能感受到他压抑的狂潮翻涌而来。
他就像一头需索无度的猎豹,饿极了,丧失了理智。仿佛我们身处一叶扁舟上,在举目无涯的海面漂浮,波浪卷动着船身,浮浮沉沉,一次又一次,从高处到低谷,再从低谷都高处,狂风暴雨不外如此。是了,这就是那无法回头的苦海,他在彼岸,他在我怀中,我终究是没有回头,向他迎了过去。
两人的身体无比契合,破浪滔天中,在苦海里翻滚,似乎要将这一年积欠下的统统填补回来。当风浪逐渐平息下来时,两人都重喘着气,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像抵死纠缠的兽。
他突然唇压下,凑近我的耳:“敏敏,我以后都唤你敏敏,好吗?”
“好。”从未有人如此唤过我,老爹和小叔叔都唤我小敏,宁一他们唤我敏子,而他。。。。。。一直连名带姓的唤,而今这个称呼,算不算是他的专属?
在我臆想发呆间,突听他的气息扑在耳廓,声音穿透耳膜:“敏敏,我们生个孩子吧。”全身血液冻住,原本灼热的身体瞬间发凉。
孩子。。。。。。我能拥有吗?会不会有遗传?这个问题从未考虑过,而此刻却不得不拿出来思虑。他不说我还没想到,刚刚爱得太疯狂,两人的情绪都扬在高处,完全就忘了做保护措施这回事。以前他不愿要孩子,我会觉得心伤落寞,现在他想要孩子,我依然觉得难过。
原本在走进院子看到他背身坐在台阶,而后又听他呜咽着祈求时,心防彻底被冲垮。所有的坚持都化为乌有,在决定抱住他的那刻,侥幸地想或许。。。。。。事情不会那么糟,医生也说了是生一次重病,生命力就减弱一分,那我只要注意好了,保护好这玻璃似的身体,可能不止活十年二十年呢。就算真的没办法预防,那也有十几年的岁月,能够拥有他十几年,能够再爱他十几年,也觉足够了。
自欺欺人也好,掩耳盗铃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对那样的他说一句残忍的话,一个字都不行,只想就这么抱着他吧,成全他渴求的“机会”,也成全自己心底永不熄灭的火苗。可是拥抱过后,孩子这事首当其冲被提起,就如一盆凉水从头将我浇到脚。
如果我因为这身体而不能拥有孩子,那么这个没有背弃的婚姻里,我还能给子杰什么?而如果我能生育,将来的某天,不仅让子杰失去了妻子,还让孩子失去了母亲。
侧转脸没敢把心慌表露,而他将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许,竟是情潮又起,唇悉悉索索地从耳后移到脖子。这一次原谅我无法专心,脑子里全是孩子那个问题,几分钟后,他也发觉了我的不专心,贴在耳朵边问:“你在想什么?”
心头发慌,脑中翻找着理由,总算被我找到了,“晚上还要上班,不要再。。。。。。了吧。”
“再什么?嗯?”他声音里含了坏笑,我面上一热,又听他说:“今晚就别去了,我打个电话给秦周。”
我直觉否定:“不要!”这电话一打,还不昭告天下了我们的关系?虽然之前他说我们的婚并没有离,就算现在这样抱在一起也是合法的正常夫妻生活,可在这之前我和他都表现了一副漠然不识的姿态,然后转个身亲密展现,那太窘迫了。
秦周可能在昨天之后觉出了点苗头,但也不会想到隔日这个人与我就那个啥了。
回神间发现身后的人一直没再有动静,一转头就见他眯着眼,深蹙着眉盯我看。莫名心虚而起,视线避闪开,好半响他轻叹,但也终没说什么,只是从后抱紧了我道:“困了,睡觉吧。”一宿没睡,刚才又折腾了将近一上午,是有些困意。
但想到一事,不由问:“你早上没吃,肚子饿不饿?要去给你做点吃的不?”
“敏敏,一夜不睡你难道不累?要是睡不着,那咱们就做点别的。”
我立即噤声,转而又惊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一夜没睡?”他没好气地撇嘴,“我就坐你屋外门槛上,里面动静听得一清二楚,你坐那椅子里一动都没动过,别说你坐着也能睡。”
“。。。。。。”
19。鲟鱼有刺(为尘烟更)()
这一觉睡下,就昏天黑地的,中间到底没拗得过他,还是又办了回事。于是等到睡醒睁眼时,眼前已是一片漆黑,片刻的恍惚后想起了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事,就像是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走了过场。
身旁的位置已经空无一人,且温度都消失了,仿佛之前做了一场梦,而今梦散了无痕。忽略掉心间的抽动,起身下地,翻找了好一会,也没找到自己的手机。再扭头看看外面沉浓的天色,轻叹了声,想也知道定是过上班时间了,好好想个迟到的理由吧。
从卧室走出,被外屋的灯亮耀了下眼,恍过眼适应了明暗后才定目,环视了一圈,似听到厨房传来声音,脚步随心移动,走到厨房门口凝住视线。那个刚才以为走掉的男人,正穿着我的围裙,手持锅铲翻炒着什么,忙碌的不可开交。
踮起脚尖看了看,锅里一片碧绿,印象中我的冰箱里好像没什么储备了,正合计着要去采购一番,他这是出去买的菜?问题是,他竟也会做菜?!
转眸看向旁边的炉灶,上面似闷着什么,香味已经飘散而开,循循诱人。忍不住做了个吞咽口水的动作,原本背朝门的男人骤然回头,目光焦灼在我身上,“醒了?去梳洗下吧,出来就能吃了。”
我略一迟疑,还是开口:“那个。。。。。。我要去上班了,就不吃了。。。。。。吧。”在我拒绝的当口,他转身揭开了那边闷盖着的锅盖,原本隐隐约约透过来的香味,顿时扑面而来,是我最爱吃的清蒸鲟鱼,这回不再是小心吞咽口水了,肚子里的馋虫纷纷爬起。
“秦周那我已经给你请了假,放心,并没有以我名义,是用你手机发的短信,手机就放在外面的桌上。”他头也没回地交代着,我朝桌面看了看,确实遍寻不着的手机躺在那。回眸再看他坚挺的身背时,有些怔忡,虽然看不到他神色,但从刚才那话中觉摸出了点异样来,张了口又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最终还是慢了好几拍的轻嗯了声,算是应答。
晃神中进到洗手间,抬眼看向镜中的自己时,直接被雷到了。难怪他刚才转身看到我就“建议”梳洗呢,那头发跟个乱毛草一般堆叠着,这还是其次,脸上还爬着好多条泪痕。早晨没控制泪意泛滥,之后两人就抵死纠缠,再后来相拥而眠,痕迹就这么“保存”了下来。
视线再往下,我哀嚎了。从脖颈处开始,红痕一路延伸,直往衣服底下钻,是个过来人都能明白那红痕代表了什么。足见之前某人是有多疯狂!幸亏没有坚持出门,这幅光景若是被馆里同事看到,立即我就成那头号八卦对象。
磨蹭了好一会,才从洗手间出来,子杰已经坐在了桌边等着,两菜一汤均已上桌。无论从色到香而看,都应是不错,夹了块鱼肉一尝,自卑了,他做得菜居然比我都还要好吃!
还是没忍住开口询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了?”之前和他一起时,从没见他动过铲子,如果我不做,两人就是喊外卖吃,自然而然就以为他信奉君子远庖厨的理念了。只见他筷子顿了顿,遂又夹了块鱼肉放到我碗里才说:“就最近学的。”
啊?最近?我不由瞪眼,看看桌上的菜,再看看他神情,不像有假。“你有去报考厨师班?”要不能学这么快?他却道:“没有,就网上看了看大致做法,做过几次就会了。”
我直接埋头吃饭,大口咬碗里的鱼肉。再问下去,就是自个找侮辱了,可对面的男人却不放过我,似调侃似炫耀地说:“很多事,其实都需要天赋的。”
他这话说得就跟当初与我比赛射击时一样的。。。。。。傲娇,让我很是磨牙霍霍。
然而牙没磨成,我被鱼刺给卡喉了,从轻咳到重咳,后来发展成了猛咳,眼泪都咳出来了,也没能把鱼刺给吐出来。子杰一边拍我后背,一边担忧道:“你怎么回事呢,吃个鱼也能被刺给卡了。”我无力去反驳他,刺梗在喉的痛苦,无法言表。每一下吞咽,哪怕是口水,都似折磨着喉咙处。
尝试了吞咽饭、喝酸醋等几种土办法后,最终均无效,只能去医院。好好的一顿色香味俱全的晚餐,就这么泡汤了,也算是小小报复了下某人的“天赋”论,就是代价很是痛苦。去到医院后,医生用手电筒照了半饷,说刺扎得很深,得下麻药。
一听麻药两字,我就腿软了,不是吧,取个鱼刺用得着动手术吗?试想了下喉咙口割开的画面,打了个寒颤,太小题大作了。
医生开好取药的单子后,我赖在椅子上不肯动,坚决摇头声称没多大事,忍忍就过去了。子杰在旁耐着性子问我为什么不去打麻药,说话都不利索了,还硬撑什么。我默了下把想法跟他一说,他还没开口,旁边医生就忍不住插嘴了:“谁跟你说打麻药是要动手术了?”
我怔住,迟疑地转头去看医生,只听他又解释道:“你这种情形只需喷洒麻药后,利用电子喉镜来取。”咦?不用动手术?好吧,我听到麻药就直觉反应成手术了。
乖乖跟着去取药,再回来进了检查室,打上麻药后。。。。。。
等从检查室出来,我的腿更软了,脑中只有两个字:可怕!从小到大没做过什么喉镜,听那表面意思以为就是拿个什么仪器在外头照照而已,哪知根本不是如此。居然是用管子穿过鼻腔进入喉咙处检查!从那台上爬下来时,鱼刺是除了,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一大把。
这不是坚忍不坚忍的问题,而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一根管子那么捣弄着,还吊在喉咙口,一下接着一下的干呕,撕心裂肺。
出门就冲进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