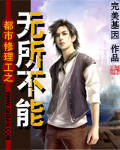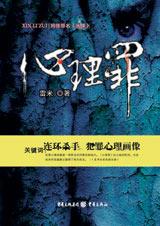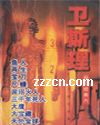物权法原理-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还要求我们依中国的实际而建立各项物权制度。例如,关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宜根据我国的实际并追随现代法律发展的潮流,而采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之结合,而不采德国民法所谓物权变动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关于用益物权,宜以物权关系固定农地使用关系,称为农地使用权;宜以物权关系固定国有土地和农村宅基地使用关系,称为基地使用权。此外从我国的现实出发,还应废除习惯法上的典权,等等。
(二)面向21世纪。我国是在20世纪即将降下帷幕,21世纪即将开始的新旧递嬗之际制定物权法,因此这部物权法除须反映我国现实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外,还应将视角着眼于21世纪,即制定面向21世纪的物权法。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那时我国势将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社会关系势将更趋复杂,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也势必会层出不穷,纷至沓来。有鉴于此,如何使这部物权法能应付裕如的适合于21世纪,也就成为我国物权立法之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其中尤其对于物权法定主义,必须表明立场。
物权法定主义,其目的非在于僵化物权,使物权的类型与内容嘎然截止在立法之际的门槛内,局限于立法当时所确定的物权类型的藩篱里,由此阻止法律的发展。相反,它旨在通过固定物权的类型与内容,来限制当事人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新的法律关系,从而达到使物权关系臻于明确、安定之目的。但这并不排除于必要之时,可依补充立法或法官造法的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为唯有如此,物权法才能与时俱进并因应社会的需要而不至与社会脱节。概言之,物权法定主义,我国固应继续维持,但为使该主义不至陷于僵化而与社会生活之需要发生龃龉,乃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有条件的承认社会惯性上新产生的物权的适法性,即采物权法定主义之缓和。
(三)注意物权法的发展趋势。鉴于物权法,尤其是其中的担保物权法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出现了国际化的潮流与发展趋势,故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必须对此予以关注,尤其应当注意借鉴各国家和地区关于担保物权的共通性规定。如关于各种特殊抵押权——共同抵押、财团抵押、企业担保、证券抵押、最高限额抵押的规定,以及关于各种特殊留置权的规定,等等。关于用益物权,应注意借鉴现代各国关于空间权的规定,规定空间得为权利的客体,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空间f所有权、空间地上权及空间(地)役权制度。
(四)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的立法思想,同时兼顾社会公益。民法自罗马法以来,有所谓本位问题。民法的本位,亦即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或基本任务。由民法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物权法为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有所谓本位问题。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注意各国家和地区物权法本位问题的发展潮流,我国制定物权法,似应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的立法思想,并同时兼顾社会公益。
前面已经谈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既无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同时也未真正进行过这方面的立法。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乃相继制定了若干重要民法制度,尤其是1986年颁行了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完全是以权利本位作为中心的立法。当然,民法通则此外也有体现社会本位思想的规定,如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关于权利滥用的禁止原则,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无过错责任等等。这些均无不表明民法通则在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法人民事权利的保护的同时,也提出了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要求,不允许滥用权利以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益。毫无疑义,我国制定物权法,应当继续坚持这一立法方向。
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为权利主体直接支配财产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恒涉及权利主体以外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自近代以来,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物权思想的发展轨迹是:由个人主义的物权思想到团体主义的物权思想,再到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协调发展的物权思想。
18、19世纪近代肇端之初,欧陆各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激荡并达登峰造极之程度,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与解放。在这种氛围下,物权立法系以个人主义作为立法的中心,结果形成称之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的财产所有权绝对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当时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但至19世纪末,因支撑物权法律制度的社会物质基础发生变迁,时移势易,物权观念遂由个人移向社会。认为物权之终极目的不全在保护个人之自由与权利,同时对于整个社会之发展与人类的生存,亦应兼顾。于是物权立法遂由个人主义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主义、团体主义为中心。但是,社会主义的、团体主义的物权立法思想,其初衷虽然在于匡正个人主义权利思想之缺失,但这一思想本身犹如带有两面锋刃之利剑,如用之不当,适足以抹杀私人财产权,戕害个人自由。因此新近以来,学说遂倡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协调发展的物权思想。这一思想,不独是现代物权立法思想的主流,而且也必将成为21世纪物权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关于此,本书将于“所有权通说”一章作详尽论述,于此不赘。
我国的情形与上述欧陆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显不相同。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曾有过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传统(这种封建专制传统的显特征是重公权益,轻私权益,对庶民个人的利益缺乏严格的保护和依法调整的观念,国家利益是地主、官僚、贵族利益的集中体现,是至高无上的。而私权益即庶民个人的利益却受到严重漠视。譬如民间发生财产纠纷,法律认定为“细事”、“细故”,一般采取调处解决,而无须告官,即使经官也缺乏严密的法律调整,经常是援引习惯、礼制进行判决。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太革命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否定个人利益和权j利,近乎彻底的社会本位,故而致我国现今权利及权利保护观念,不甚发达。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建议制定物权法时以权利本位作为立法的中心,于此基础上兼顾社会公益。关于此,本书第七章将作详尽论述。
第8章 物权的客体(1)()
(第一节物权的客体
一、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为民事权利(私权)之一重要类型,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在民法上,凡民事权利均有其客体或标的物。债权的客体为行为,称为给付,但在多数情形,给付仍以物为其标的,称为标的物。人格权的客体为存在于权利人自身的人格利益;身份权的客体为一定身份关系上的利益。物权由性质所决定,其客体为物。
说物权的客体为物,也就意味着权利不属于物权客体之范围。近代以来,虽然物权中的权利质权、权利抵押权的客体为可让与的债权或其他权利,如土地使用权、地上权、采矿权、永佃权乃至典权等等,但是,权利质权、权利抵押权这些存在于权利上的权利,从来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物权,相反,立法理念与立法政策历来是将其作为普通质权(动产质权)或普通抵押权的特殊情形而处理的,并使之准用有关普通质权(动产质权)或普通抵押权的规定,故属于准物权范畴。可见,绝不能因权利质权、权利抵押权之客体为权利,而就因此日物权的客体不以物为限,而还包括所谓权利。
在此有必要提出的是,我国现行某些涉及“物权”的民事法律关于“物权”的客体多不使用“物”这一概念,而大都使用“财产”一词。如,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关于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就迳直使用“财产”一词,谓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担保法第三章“抵押”、第四章“质押”及第五章“留置”,也都称抵押权、质押权及留置权的客体为“财产”。虽然这些场合中的“财产”,大体上即是我们所理解的“物”,但在多数情形下,“财产”之外延均较“物”的范围为广,不仅包括有体物如机器、交通运输工具等,而且也包括抵押j人有权依法处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向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及荒滩等所谓“四荒”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于此可见,我国现行法所谓“财产”,其范围大抵包括了上述“物权”及“准物权”的客体范围。
二、物的意义
(一)物的概念
关于何为民法上之物;自罗马法以来,大抵形成了三种立法例:一是以罗马法及法国民法为代表的立法例,认为物不仅包括有体物,并也包括无体物(盖优士gaius在法学提要中写道:能触知之物为有体物rescorporalcs,不能触知之物为无体物resincorporales;法国民法典第517条。);=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例(参见日本民法第85条,德国民法典第90条。),认为物仅指有体物;三是以瑞士为代表的立法例,认为物既包括有体物,同时也包括“法律上可得支配的自然力”。
以上各种立法例,以第三种立法例为多数立法例。上面已经提到,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与担保法均未使用“物”这一概念而是称为“财产”。唯制定物权法时,为使物权法之体系结构臻于和谐、完善,并使各项物权概念臻手科学,实有必要改变现行做法,将“财产”改称为“物”。因之,探究物的概念问题无疑有其重要意义。综合近现代各国民法立法及学说理论,关于物的概念,论者认为似可界定如下:物,是指存在于人体之外、人力所能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及自然力。据此定义,可知物的概念具有下述特征:
1。非人格性。近代肇端以来,法律思想以个人尊严为基本原理和出发点而予以构成,人之身体为人格所附,不属于物,故生存中之人的身体或其一部,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按照现代法律,自然人既不能以自己之身体为客体成立所有权,同时原则上也对自己的身体无处分权。)。于他人之身体上成立物权,无异于承认奴隶制度,为现代法所不许。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人之身体不属于物的观念正日益受到挑战。如器官移植、。器官捐赠、献血及所谓代孕母等,均以活人之器官为契约的标的物。晚近学说认为,此等契约是否有效,应视其是否背于公序良俗而定,如不违于公序良俗者,即为有效,反之为无效。另外,生前处分自己遗骸的契约或遗嘱,如不与公序良俗相违时,亦属有效,如生前约定将自己死后留下的遗骸供医学研究,即为适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失去生命之尸体,现代各国法律多认为属于物(但德国实务与学说系采否定立场,不认尸体为物,而认为是人格的延续部分或扩展部分,对人的尸体之侵害仍构成对人格的侵害。参见梁慧星主编,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由继承人“所有”。惟此所谓“所有”,实质上不过为一种习惯上的“管理权”,即继承人对于失去生命之尸体仅有依习惯祭祀予以埋葬、焚化或将之供作医学研究使用的权利。可见“尸体所有权”,与一般物的所有权有相当大的不同。一般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得对标的物为自由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而尸体所有权,所有权人对作为标的物的尸体则无此等权利。参见'日'本城武雄等:民法总则,嵯峨野书院1996年版,第118页;大判昭2。5。27民集6。307,最判平元7。18家。41。10。128。)。
问题在于,以活人身体之一部为标的物的契约能否强制执行。新近通说认为,为输血之血液买卖、为移植之皮肤切取,或眼角膜、肾脏之捐献,于不至造成重伤的限度内可有效成立,但为了维护人之价值与尊严,绝不能赋予受移植人由移植人之活体强行取去之权利,亦即不准强制执行。
2。原则上须具有有体性。即民法上之物原则上以有体物为限。法制史上,物之区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系由罗马法为其端绪,其后为法国法系民法所承袭。所谓有体物,指占据一定空间,可为人力所能支配的物质。无体物,指不能触觉之物,如专利、商标、著作、营业秘密、konw…how(专有技术)、信息等均属之。无体物,原则上不能作为民法上:之物。
但是,这一原则同时存在以下例外:一是电、热、声、光等能源,以在法律上有排他的支配可能性为限,被视为物。如前所述,瑞士民法就此设有明文;二是特定的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由平面利用转向主要进行立体利用,空间权概念应运而生。通说认为,空间——无论是土地的空中或地中,如果具备独立的经济价值及排他的支配可能性两要件,即可成为物。
3。支配可能性。即民法上之物,应是人力所能支配的物,人力不能支配的物,如日月星辰等虽为有体,但非人力所能支配,故仅为物理上的物,而非法律上的物。法律上的物既然重视物与人的关系,则物必须有被支配的可能。没有支配可能性的物,决不能成为法律上之物。
4。独立性。即必须独立成为一体,且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物质,才能成为民法上的物。如一粒米、一滴水,虽为物理上之物,但因不能独立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活需要,故不能谓为法律上之物。椅子之脚,屋之梁、柱、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