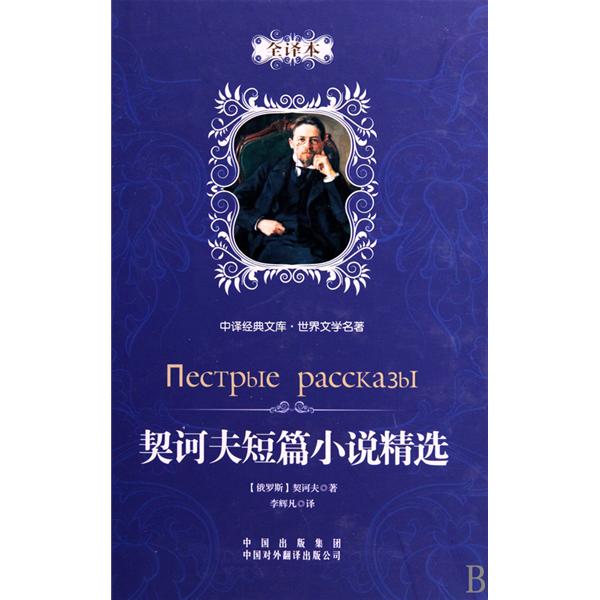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全集-第1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天,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他梦见自己亲手给邻居安东造了一幢房屋,银子盖顶。孩子们再不以恐惧的眼光看他了。
九
早晨,他雇了两个农民,便一起进山了。
他走到深渊边缘,在腰上系好绳子,对两个农民说:
“你们把我放到下面去!”
他们惊奇地凝视着他。
怎么?他要下深渊!他竟要下这个深渊!难道他竟不晓得在这儿曾经发生过可怕的凶杀吗?强盗们杀死了一个商人,抢了他。杀人凶手、被害人和抢的东西,像沉入海底一样,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唯有殷红的血迹。下深渊?谁也不会想到干这种事呀!可他竟为了一个纽扣就要
“把我放下去!”丢失纽扣的人说道。
“你清醒点!”
“放呀!不然我跳下去。”
两个农民想了想。年长的农民说:
“让他下去吧,这样少惹祸。”
他提着灯开始往下爬。
起初挺艰难。他越往下去,越黑暗,可反倒轻松容易了。他抓着陡峭的石壁攀援,好像感觉到有某种物体轻悄地从他手上滑去。
“啊,大地!即使这里面也有生命!”
随即他点燃了提灯。
一片峭壁,就要到底层了。
渊底平坦而狭窄,堆满了落下来的石块。没有发现尸骨,只有峭壁缝里流出的水声潺潺,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可他并不惧怕这神秘的声音。
他开始找纽扣了。
他突然纵身一跳呼喊起来。
那颗纽扣映入了他的眼帘,仿佛有人特意放到这儿的。纽扣旁边还有一条旧口袋。
提灯脱手摔碎了,也熄灭了。
他一伸手就摸到了那个纽扣!他拾起纽扣,翻来覆去地抚摸着。
对,就是它!正是他丢掉的那只纽扣!
他找到了纽扣之后,透过深渊仰望着天空。刹时间,他眼中的天空又跟往常一样,那么光彩夺目,晴朗诱人。
他定了定神,恢复了常态,抓住一个似乎是破提灯的东西,发出了信号,以便上边两个农民拖他上去。
两个农民依靠几个偶然过路人的帮助,很快拖他上来了。
他刚一上来就把一个灰色的小东西给大家看,说道:
“就是这个!”
那几个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仔细瞧瞧!”
大家所见到的正是同他上衣上其他纽扣完全一模一样的纽扣。
他们一起赶紧回来。村头有人问道:
“为啥把提灯装进袋子里?”
“是啊,这只袋子就放在我纽扣的旁边。也许我弄错了,竟把它当做提灯了。噢,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吧!”
他说着就打开了袋子。
原来袋子里装的全是光闪闪的大金币!
十
整个小镇都哗然了。
“哼,这回又得望天了。准会跟先前那样又自信,又自爱。干吗让这个怪人发财?他准得修一座直冲九霄的高塔,塔上再放一架望远镜,好从望远镜里看月亮,望星星。可他倒不帮助亲生父亲。”
他找到了纽扣之后,首先救济邻居老安东和他生活在烟熏火燎的茅屋里的穷困一家人。而后他想起他在寻找纽扣时在穷人家里亲眼目睹的一切苦难。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善于公平合理地施舍这些金币。他几乎把全部金币都施舍给自己家人和外人,这里面有爱惜他的人,也有捉弄取笑过他的人。
他将这只纽扣缝在衣服原来的位置,依然每晚外出散步,一只手依旧抚弄着胸前那只纽扣。不过,他已经不单单望着天空了,而今使他关心的还有大地和人类。他感谢天地各自的功绩。
每逢春天将临,灌木嫩芽放绿之时,他便钻进山坡树丛中。
他小心翼翼地搬开大石头,两手扶地,屏住气息,观察着千奇百怪的虫类。他听见鸟儿在自己窝巢旁歌唱时,就取笑般地说:
“灰色的小纽扣!”
父亲一边不时地望着我,一边讲了这个故事。
不过只是到后来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
高韧译
作品简析
第一章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19世纪初俄国大作家、俄罗斯近代文学的莫基人。出生于莫斯科一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的影响,思想激进,曾被沙皇流放到南方。1837年1月29日与一流亡俄国的法国人决斗后重伤身亡,年纪不到40岁。普希金于中学生时代步入文坛,才华过人,在诗歌、戏剧、等方面都大有建树,成了俄罗斯文学从古代进入近代,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转折时期最卓越的代表。最主要的代表作有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茨冈和铜骑士,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诗体叶甫盖尼奥涅金,散文体别尔金集、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及大量抒情诗。
驿站长
十四品文官帝俄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驿站的独裁者。
——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维亚捷姆斯基公爵(1792—1878),俄国诗人,评论家,这两句诗引自他的诗驿站。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骂过架?谁没有在气愤的时候向他们索取过那要命的本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压制、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谁不把他们当做人类的恶棍,犹如过去衙门里的师爷,或者,至少也和摩罗姆的强盗当时的农奴为了逃避地主的压迫,常常结伙为强盗。奥卡河上的摩罗姆森林里,因常有这样的强盗出没而驰名。无异?但是,我们如果公平一些,尽量为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许,我们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得多。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十四品的真正的受气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而且这也并非总能做到(请读者扪心自问)。维亚捷姆斯基开玩笑称他是独裁者,他的职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在枯燥乏味的旅途中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在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错。旅客走进他贫寒的住所,像望着敌人似地望着他。要是他能赶快打发掉这个不速之客,还好;但是如果正碰上没有马呢天哪!咒骂、威吓就会劈头盖脸而来!他得冒着雨、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奔走。遇上狂风暴雨天气或是受洗节前后的严寒日子指一月下半月最寒冷的时节。他得躲进穿堂间,只是为了休息片刻,避开激怒的投宿客人的叫嚷和推搡。来了一位将军,浑身发抖的驿站长就得给他最后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包括一辆急行车。将军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是铃声一个信使把自己的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好好地想一想,那么我们心里就会怒气消释而充满真挚的同情。我再说几句:连续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目前我只想说,人们对驿站长阶层的看法是很错误的。这些备受诽谤的驿站长,一般来说都是和善的人,生性愿意为人效劳,容易相处,对荣誉看得很淡泊,不太爱钱财。从他们的言谈(不巧得很,过路的老爷们却瞧不起这种言谈)中,可以吸取许多有趣的东西,得到许多教益。至于我呢,我是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要听一位因公外出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属于可尊敬的驿站长阶层的。真的,有一位驿站长给我留下了很珍贵的记忆。我们曾有机缘一度相识,我现在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他的故事。
1816年5月,我曾经乘车在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驿道上经过某省。我官卑职小,只能乘驿车,只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钱。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常常要经过力争才能得到我认为是我名分应得的东西。当时我由于年少气盛,要是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匹马套到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对他的低贱和胆怯就感到愤慨;在省长的宴会上,如果善于辨别身份的仆人上菜时把我漏掉,我也总是耿耿于怀。如今呢,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真的,“按官阶论等”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如果用另一条规律,比方说,用“凭才智论等”来代替它,那我们会碰到什么事呢?会发生怎样的争论啊!仆人上菜又从谁开始呢?但我还是回过来讲我的故事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某驿站还有三俄里的时候开始落下稀疏的雨点。转眼之间,倾盆大雨已经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要一杯茶。“嗳,杜妮亚杜尼亚是阿芙多季娅的小名。”驿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点奶油来。”一听到这两句话,从隔扇后面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跑到穿堂间里去了。她的美丽使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回答说,“她聪明、伶俐,跟过世了的母亲一模一样。”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就欣赏起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来。它们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见新约全书中的路加福音。第一幅画上画着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给一个样子浮躁的青年送行,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口袋金钱。另一幅画以鲜明的线条画出这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这个把钱挥霍尽了的青年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和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伤和忏悔。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如此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相当不错的德文诗句。这一切,还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什物,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中。这位五十来岁的主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我还没有跟送我的老车夫把账算清,杜妮亚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他父亲喝一杯潘趣酒用沸糖酒加糖水、果子露等制成的混合饮料。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人就聊起天来,仿佛认识了很久似的。
马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仍旧不愿意同驿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最后我同他们告别了;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车。到穿堂间里我停下来,请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从我做这件事以来,我曾有过许多次亲吻,但是没有一次亲吻,曾在我心中留下这样悠长、这样愉快的回忆。
过了几年,机缘又把我带到那条驿道,使我重临旧地。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想到又可以看到她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又想,老驿站长也许已被撤换,杜妮亚大概已经出嫁。我的头脑里也闪过他或她会不会死去的念头。我怀着悲伤的预感走近驿站。
马在驿站前停下。一走进房间,我立刻认出了那几张描绘浪子回头的故事的画,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驿站长盖着皮袄睡着;我的到来把他惊醒,他稍稍抬起身来这正是萨姆松维林,但是他衰老得多么厉害啊!在他准备抄下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花白的头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的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你认得我吗?”我问他。“我和你是老相识了。”“可能。”他阴沉地回答道,“这里是大路,来往旅客到过我这里的很多。”“你的杜妮亚好吗?”我继续问。老头的眉头皱起来了。“天知道她。”他回答说。“这么说她是嫁人了?”我说。老头装作没有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轻声念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吩咐烧茶。好奇心开始使我不得安宁,我希望潘趣酒能使我的老相识开口。
我没有想错,老头没有拒绝送过去的杯子。我发觉甜酒驱散了他的阴郁。一杯下肚,他变得爱说话了。不知是他记起来了呢,还是装出记起我的样子,于是我便从他口中知道了当时强烈吸引了我并且使我深为感动的故事。
“这样说来,您认识我的杜妮亚罗?”他开始讲了,“有谁不认识她呢?唉,杜妮亚,杜妮亚!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以前,凡是过路的人,都要夸她,谁也不会说她不好。太太们有的送她一块小手帕,有的送她一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好像要用午餐或是晚餐,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不管火气多么大的老爷,一看见她就会平静下来,宽厚地同我谈话。您相信吗?先生:信使们跟她一谈就是半个钟头。家由她管:收拾房子啦,做饭啦,样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这个老傻瓜,对她看也看不厌,有时,连喜欢都喜欢不过来;是我不爱我的杜妮亚,不疼我的孩子呢,还是她的日子过得不称心呢?都不是,灾祸是躲不了的;命该如此,要逃也逃不了!”于是他开始向我倾诉他的痛苦。
三年前,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驿站长正在一本新的簿子上划格子。他的女儿在隔扇后面给自己缝衣服,这时候,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契尔克斯帽、身穿军外套、裹着披肩的旅客走进来要马。马都派出去了。一听说没马,旅客就提高嗓门,扬起了马鞭。见惯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扇后面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