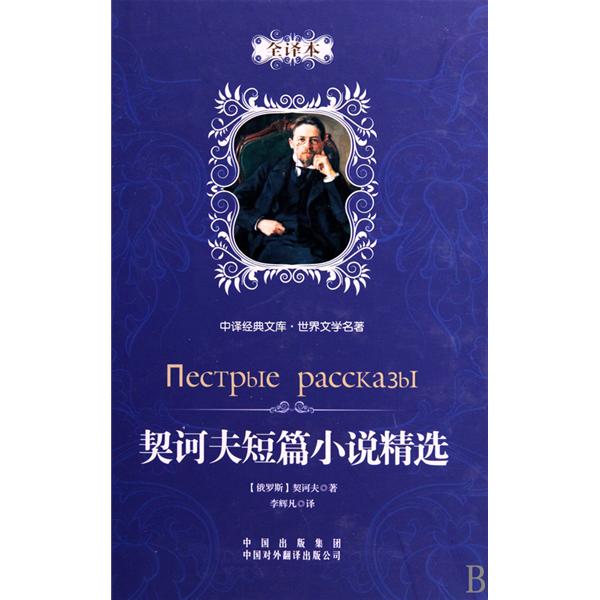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全集-第19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打心坎上笑我们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时,一个叫花子走了进来。他用歌唱的调子发出一阵悠长的哀叹。
我母亲笑得几乎昏过去了。
“算了吧,我的好人,”她说道,“我在这儿糟蹋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需要一个铜板。少了它就买不到半磅肥皂。”
那个叫花子,一个脸色温和的老头儿,瞪着眼睛看着她。
“一个铜板?”他问道。
“是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
“这还了得,接受一个叫花子的布施!”
“不要紧,我的姑娘。我不会短少这一个铜板的。我短少的是一铲子土乞丐指得是埋葬自己的坟土。有了这,就万事大吉了。”
他把一个铜板放在我的手里,然后满怀着感恩的心情蹒跚地走开去了。
“好吧,感谢上帝,”我母亲说道,“再没有”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大大发出一阵笑声。
“钱来得正是时候!今天再也洗不成衣服了。天黑了,我连灯油也没有!”
她笑得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窒息。她弯着腰把脸埋在手掌里,我去扶她的时候,一种热乎乎的东西流过我的手。
那是血,是我母亲的血,是她宝贵的、圣洁的血。我的母亲呀,就连穷人中间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样会笑的。
凌山译
作品简析
第一章 斯特凡·勃努内斯库()
斯特凡勃努内斯库(1929—),罗马尼亚当代着名散文家和家。出身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担任过编辑和记者。1968年至1971年间,任金星杂志主编。早期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报告文学的创作。1963年开始创作,出版了男子汉的冬天(1965年)和乡村来信(1976年)等数十部集,曾多次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大奖。
从前的暴风雪
“当你听到某人说从前的雪下得更大,他的青年时代是另一番模样等等等等时,为了赶紧结束谈话,你会随声附和他的说法,可你心里觉得你面对的是一个开始衰老的人。他判断事物的唯一尺度存在于遥远的过去,这意味着就连这样一件陈旧的器具他手头也没有。事实上,他是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能有什么看法。”我对友人说。我正在他家度寒假哩。“我能有什么看法,这些都是些平庸的琐事,我们可别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时间。”
“可不能这么说,”友人说,“倘若你开始厌烦,对这些平凡事物提不起兴趣,这才叫平庸哩。要知道,它们也有它们的价值。比方说,从前的暴风雪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
“得了得了,”我笑着对友人说,“看来你也开始衰老了,你也成了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从前的暴风雪!”
“没错,从前的暴风雪。我们为何不承认暴风雪并不全都一样的呢?从前的暴风雪,亲爱的,从星期一下午开始,一直要到星期六早晨才结束有一回,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暴风雪到来了”
“你想说说笑话吧。”我试图打住友人的话头,生怕他会给我讲一个什么老掉牙的故事。
“噢,”友人不慌不忙地继续讲道,“那时我还很年轻,一场暴风雪降临了,天哪,那是怎样的一场暴风雪啊!正是这样,从星期一下午开始的。我特意对了一下表,以便密切关注一下这场暴风雪,好像,让我想想,那是星期一下午六点差十分。我等待着。寒风呼啸,大雪纷飞,飘散的白雪一会儿落在地上,一会儿又打着圈儿飞了起来,白昼顿时变成了一个白晃晃的夜晚,布满了芒刺,使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屋里的炉子不再烧了,只有烟雾弥漫,灯光和蜡烛熄灭了,你的心中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怖。我失去了时间概念,表早已停了,我想暴风雪开始后没多久,我听见了猛烈的敲门声。那是绝望者的敲门声。可能是一个迷路者,我寻思——就像数不胜数的民间故事中发生的那样。但我并没有急于去开门。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何许人。然而,猛烈的敲门声又一次响起。”
“你是谁?”我问道。
“你的一位兄弟。”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胡说八道,”我对门外的人说,“你最好说清楚你是谁。”
“你的一位兄弟。”陌生声音重复道。
“就算你是,”我说着打开了门,“就算你是一只被羊吃了的狼吧,请进来。”
走进屋来的是一个魁梧的汉子,身穿一件翻毛皮大衣,皮衣、眉毛、下巴和胡须上结满了钉子大的冰凌。我帮他脱下衣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为他脱下了皮大衣,因为他已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像根木头。最后,我使尽浑身解数,让他恢复精力,暖和身体,重新像个人样。他也真的恢复了过来。恢复过来后,似乎并不像刚进门时那么高大了,又获得了正常比例。
“嗨,”见他恢复体力后,我问道,“这下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了,尽管,说实话,除此之外,我也不感兴趣。欢迎你并祝你永远平安!”
“我,”陌生人执拗地说,“是你兄弟。”
我哈哈大笑,然后对他说:
“好吧,就算你是我兄弟,但是哪一个,因为我有许多弟兄。为了帮你一把,使你不至于混淆,我可以告诉你,的确,我的弟兄中有四个,也就是我的四个哥哥,我已很久没见了。就算你是我四个哥哥中的一个吧,可是,瞧,你长得同我一点也不像,实在无法把你当作我哥哥,而且,据我所知,你和他们也不像。尽管很久没见面,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们的鼻子、喉结、眼神、走路姿势以及手和头动的样子。”
“你久未谋面的四个哥哥我一个也不是,”陌生人说,“我是另一个。”
“那你就谁也不是。”我差点吼了起来。
“不,”陌生人顶了我一句,这一回摇了摇头,他的头发、眉毛、下颚、胡须上立马落下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雨,还夹着冰。“不,我是你弟弟。”
“你怎么可能是我弟弟呢?我弟弟刚出门,到院子里去取捆木柴了,他倒是披了件皮大衣出去的,可你并不是我弟弟。”
“我是的,我是你弟弟,正是从这间屋出去的,为了去取一捆木柴,但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刚刚出门,而是星期一下午,暴风雪开始的那一会儿。”
“哼,见了鬼了,”我说,“难道现在不是星期一下午吗?”
“不,现在是星期五清晨。”陌生人回答。我还是觉得他很陌生,在冒充我弟弟。“现在是星期五清晨,”他重复了一句,“我确实是星期一下午出去的,但还没等我去柴堆上取柴,我就听到街上传来一阵阵奇怪的马蹄声,还夹杂着女人和男人的声音。我朝街上走去,顺着马蹄声一直往前走,最后竟迷了路,接着发生的一切都很艰难,我实在难以启齿。最后,瞧,我又回到了家里,尽管直到今天,星期五早晨才回到家。”
屋里有点冷,我想大概火灭了,不知怎么搞的,我怒气冲冲地向他发问:
“好吧,你迷了路,就算你迷了路,但至少你从院子里取回木柴来了吧,你不正是去取木柴的吗?”
“我没取木柴。”他羞愧地说。
“行啦。”我怨恨地对他说,然后穿上衣服,出门去取木柴。我捧起一捆木柴,迅速回到屋里,既没有迷路,也没有遇到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就像我弟弟那样。我点燃炉子,然后煮了点红葡萄酒,加上胡椒粉和肉桂,打算同我弟弟一起喝上几杯。葡萄酒煮好后,我倒上两杯,朝弟弟睡觉的床走去。
“来吧,弟弟,”我摇了摇他。在我出去取木柴的时候,在我努劲点燃炉子煮葡萄酒的时候,他早已睡熟了。皮大衣翻动了一下,掉在了一边,站起身来的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根本不是我弟弟,而是另外一个人。
“你在我家干吗?”我气势汹汹地问新来的陌生人,“皮大衣下睡着的应该是我的弟弟,可却冒出了你。”
“噢,”陌生人睡意蒙眬、结结巴巴地说,“弟弟等你从院子里取木柴回来,可等呀等,一直不见你回来,就出去找你了,怕你迷路。在他等你的时候,我,你的大哥,来了,我就是你很久没见的大哥呀。我进门时,真可谓饥寒交迫,于是就对我们的弟弟说:先给我弄点热的喝和吃,然后就去找我们的兄弟,也就是你,因为我已根本动弹不了了。这样他就出去找你了,而我就盖着这件皮大衣躺下了。”
“他什么时候去找我的?”
“嗯,”我哥哥想了想说,“你是星期五早晨到院子里去取木柴的,他从星期五一直等到星期一晚上;本来星期一晚上他就想去找你,就在这时我来了,这样就耽搁到星期二早晨。没错,就是星期二早晨,我对他说:‘去吧,该去找找我们的兄弟了。’”
“那今天是星期几?”我问大哥。
“不知道,”他打着哈欠说,“不知道,因为我在小弟出去找你后,喝足,吃饱,然后倒头便睡,睡得很死很死。”
友人笑着讲完了这个故事,给我递来一杯掺香料的热葡萄酒,然后总结似的说道:
“亲爱的,这就是从前的暴风雪。你兴许会轻蔑地说这些都很平庸。然而现在倒是来场暴风雪看看,像从前那样,我到院子里去取木柴,把你留在屋里,喝着加上香料的热葡萄酒,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就出门去找我。我回来时不见你的人影,只看见喝得差不多的葡萄酒,而在你的皮大衣下,在我让你躺下的床上,一个陌生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我声称他正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斯特纳福鲁是啊,”友人一边呷着香喷喷,热腾腾的甜葡萄酒,一边怀恋地说,“是啊,斯特纳福鲁此时此刻怎么样呢?我已二十年没见他了。斯特纳福鲁,这个可怜的家伙,你还记得他吗?这家伙,对,这家伙明白从前的暴风雪意味着什么,天哪,他越是明白,讲述时就越动听,越美丽”
高兴译
作品简析
第一章 伊凡·伐佐夫()
伊凡伐佐夫(1850—1921年),保加利亚着名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戏剧家。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在罗马尼亚经商。他一生在民族解放斗争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度过,因受土耳其统治者与独裁政府迫害,曾两次流亡国外。高尔基称其是“为多灾多难的保加利亚的自由和复兴而斗争的诗人和战士”。他一生写有五十多部作品,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大战后保加利亚人民半个世纪的生活。他的长篇轭下享有世界声誉,另有戏剧名作流亡者、升官者、荣誉候选人、走向深渊、鲍里斯拉夫等。
一个保加利亚妇人——历史纪实
好啊,大娘,真是英豪!
——民歌
一
1876年5月20日,波特夫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着名领袖、革命诗人。1876年4月起义失败后,他率领一支武装队伍从罗马尼亚赶回保加利亚支援,被土耳其军队阻截挫败于伏拉察附近的巴尔干山中。牺牲在旧历5月20日,即新历6月2日。他的殉难日被定为烈士节,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的起义队伍在伏拉察附近巴尔干山的沃拉峰被击溃,而波特夫本人也被残暴的契尔卡斯契尔卡斯是住在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当时受沙皇俄国统治。头目强巴拉兹所率领的侦缉队的子弹击毙。正是那一天下午,在伊斯克尔河保加利亚西北部的一条河,向北流入多瑙河。左岸,留提勃罗德村对面的地方,站着一大群来自那个村庄的妇女。她们正等着乘船过河去。她们之中大多数人不大清楚出了什么事,有的人甚至不关心这些。两天来喧闹的侦缉队从伏拉察到这里穿梭似地来来往往,并没有打扰她们,她们还是照样去地里干活儿。真的,这儿只有妇女;男子汉是不敢出门的。尽管起义队伍和侦缉队作战的地点离留提勃罗德还相当远,但是流言也传到了这里,引起了不安,使男人们都小心起来了。今天,有几个土耳其兵到村子里捉拿嫌疑分子;在岸边渡口上,也有几个士兵监视来往的过客。这时船正在对岸,村妇们不耐烦地等船回来,好载她们过去。船终于开回来了。留提勃罗德村派来的船夫把桨往河里一撑,让船停稳在岸边,向妇女们喊道:
“喂,婆娘们,快上船吧!”
这时,在通往契洛佩克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骑马的宪兵。他们飞快地跳下马,驱散了预备上船的妇女。一个年老的肥胖的土耳其宪兵把皮鞭抽得山响,破口大骂起来。
“往后退,异教徒猪猡们!快滚开!”
妇女们闪开了,准备等下一趟船。
“从这里滚开!下贱的家伙!”另一个宪兵喊道,说罢就冲过去抡起鞭子打人。妇女们惊叫着纷纷逃走了。
这时船夫把马牵上了船。宪兵们也上去了。那个胖子对船夫愠怒地喝道:
“一只母狗也不准你摆渡过去。你们都给我滚开!”他恶狠狠地向她们挥着手。
妇女们听了这番话,都垂头丧气地向着田边转回。
“老爷,等等,等等,我求求你!”一个村妇从契洛佩克那个方向跑过来,大声喊道。
宪兵们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你要干什么,老婆子!”胖子用保加利亚语问道。
她是一个约莫六十岁的妇人,高高的个儿,骨骼突出,像男人的模样,手里抱着一个用破粗毯裹着的孩子。
“让我过河去吧,老爷!让我过去吧!愿上帝赐福给你,赐福给你和你的孩子们!”
“是你吗,伊利察?嘿,这个异教徒!”他认得她,因为在契洛佩克她替他做过奶酪酥饼。
“是我啊,哈吉*教中对朝圣者的尊称。哈桑老爷。看这个孩子的面上,让我过河去吧!”
“你带这条虫上哪儿去呀?”
“这是我的小孙子,哈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