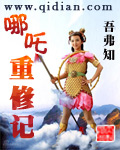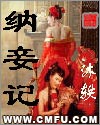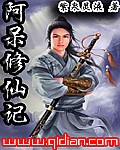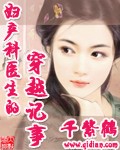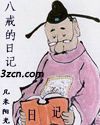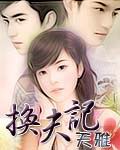ɽ�¼�-��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š�
���������Ǽ���������·���ĵ״�������ա����£�Ȼ�������Ժ�ǿ����ڹ�������ӵĴ��ڣ��Լ��ڿ���ʩ���������ʵ��³��������ʼ������������˼֮�£����߹Ŵ��й���ɫ�Ŀ���Ʊ������ˡ������ѡ��һȺ�ܸ��������Ů���͵�³������ͼ�Դ��ݵ�³��֮�ģ���䶨���Ϳ��ӵĹ�ϵ�����߹Ŵ��й���ɫ���ǣ��������ɵļƲ���³�����ڷ������ɵ��������ϣ���Ȼ��������Ч��³���Ů�֣������ϳ������������µĸ߹���Ҳ����ģ�¡�
��������·��һ����ŭ���࣬һ����ͻ����˹١�����û����·�����������ģ������뾡һ�п��ܵİ취����·��һ��ֻ���ÿ�����Щ�ǹٲ����������ǵ�����ʦ�����۳��ڣ�����ʵ�ڲ������ܿ�����ʦ�������������ҵ������С�
�����������ӵļ���Ҳ���ڲ��ò�����ʱ����·������һ���������ң���Ȼ������ʦ�뿪��³����
����������������Ҳ�����ʼҵĿ��ӣ��������н�Զ�Ķ��ǣ���������
���������������˸���֮�ڣ����Գ��ߣ��˸���֮�룬�������ܡ���
�����������������ӿ�ʼ�����������Ρ�
��������
��������һ�������ʡ��Ӻ���ʱ��Ϊ������ʸе��������˳�����ˣ����������Ͼ�����Ȼ�Ҳ����𰸡����ǹ���һ��˭Ҳ���е���ֵ�������а���������ִ����ɼ�����ʵ�����ʡ�
������ÿ�������������飬��·�Ͳ��ɵô����ĸе����ߡ�Ϊʲô��Ϊʲô��������������˵��ʹ�ƿ�һʱ�����ܻ����Ӧ��Ҳ����ȷ�����������Ӱɡ����ǣ����ѵ������������ܻ�˥�������ձ��������е�һ�����������˵õ����ʤ�������£���֪��ǰ�����������ڵ������ϼ���������û����˵����Ϊʲô��Ϊʲô���Դ�����·��˵��Ψ�����������ô�߿����Ӳ�����
���������ô��ض�������飬˼������ʲô���춼������ʲô����������������������˵Ļ����Լ�ֻ�ܷ������ˡ��������˺���֮�䲻�����������������ƺͶ�֮��Ҳ�������������ν����а���ѵ�����������֮����ʱ��Լ������·ÿ�����������ȥ�ʿ��ӣ��������һ����������һͨ������˵ʲô�����������Ҹ���
��������Ҫ�������Ļ�������Ϊ�Ƶı��𣬳���Ϊ������±����������֮����û�б�����𣿵�����ʦ���棬���ƺ��е��Լ���˵���ˣ���һ������˼�����������Dz�����������β�����Ȼ�ĵط������־�����ǿ����֮����Ҹ����������⡣�����ʿ���ܵõ�����������ü��ġ�˭���˶���˵���������ֵ��Ʊ��Ļ���һ�о�̫û����˼�ˡ�
����������������ֲ�����������ʦ�������ϸ��ܵ���Ϊǿ�ҡ��������������Ƿ��˵���λ��Ŵ�£�Ϊʲô�������������IJ����أ���ͥҲ������������֮���ò��Ĵ�Ư�������ֲ���Ϊʲô��Ҫ�䵽�������������أ�
��������һ���������������������������������ͼ�����������ӷ�ʱ����·�̲�ס����ӯ�������ӵĿ�̾��Ϊ�����²�������·�Ŀ�����Ϊ���£�ֻΪ����һ�ˡ�
��������Ϊ˹�ˡ�˹���������������·�¶��˾��ġ�Ҫ��һ���������������ֺ��б���˹�˵Ķ��ơ���Ϊ�����ϻ��ָ�����ػ��Ļر���Ҫ���Լ��������е�������������ͷ��͡��������Բ�����Ҳ�գ���֮�����Լ���ʹ�����۲�ѧ���Լ�Ҳ���Ȳ��Ϻ�ѧ����λ���ӣ�����һ�����£���Ϊ�˷�����ȴ����������ϧ��ȴ�������Լ���
���������������������һ�㡣
��������
����������������˹�������������Ƽֶ���������ӹ���ô��ʱ���������̴��������֮�գ���֮�գ��Ҵ�����Ҳ����
�����������DZ�����������̤�������й�����;�ġ������ʣ�����ĵ����Ǵ�Ҳ���ڴ��۶�����
������������·ȴ����ô�롣ͨ���ϴεľ��飬���Ѿ���ᵽ������ʵȨ��λ���϶�Ȼ�����Լ�����Ŀ�У���������һ�������ǰ���������Ǿ���һ�������ڿ������¡���������������Ļ����Լ�����ѡ���»�誡��Ļ���������������ӵ�����Ȯ��Ҳ����е�˿���ںޡ�������������Ȼ����û�У�����ǿ����ֻ�����Լ����е��������
�������и�ʽ�����������ſ��ӵ���;�����������ʵ���Ƚ�С�����غ�ij�������幡���ϲ������ƹʼ����ġ�������ɫ�ʵ��������������衣���������׳ʿ�����塣������ģ�ֻ����˵�����߾ų�����Ĵ�߸������������ʵ���Ӹᡣ���۴����䣬���Ǵ���������·���ɶ��߱���������ӵ��ʸ�
����������·�����ʮ������ӹ���λ����עĿ�IJ��ӡ�����������������ڵ��ջأ���·����˵�������ӹ���
�������ջؾ����Ǵӿ������ϳ����ǿ�͵���������������֮�����һ�����ӣ�����·����̫ϲ�������ⲻ�dz��ڼ��ʣ���Ȼ�ӹ�������֮��������ʦ���ջ����ֲ�ͬѰ�������ԣ��ƺ���ôҲ���Ʋ�ס���ָ��飩����·�����ǵ����䶼���̫Զ�����������Ƕ���Щ�²�����ĸ��ԡ���ֻ����ȫ�㲻���ջ����ֱ����͵��������ܾ����������
���������ȣ�����ȱ�ٻ�����һ��Ϳ�����ȥ��Ҫ˵�������Ȼ��Щ�ḡ�������dz���������������ӹ�������·��Ƣ�������������ͷ��֮������������·һ���˸е��Ծ�����Ȼ�����ԣ���ͷ����ȣ��˸�Զδ���죬��������������⡣��ʱ��·Ҳ����Է������ḡ���̲�ס������ͷ���ȣ��������ϣ�����������˱���һ�ֺ�����η�ĸ��顣
������ij�Σ��ӹ��Զ������������������������������Ȼ˵�ɻ��ɱ棬�������Լ��ı�ž������������Ҫ����ġ��������������ȫ��ͬ������ı����Ϊ���ɹ��ڴ�Ŀ�����Ի�����������ܣ�ȴ���������������˷�����ȫ����������ȫ��һ�������ı�Ų������������ž����������ɵĺ��أ���г�ʣ���ӵ�к�����̵�Ʃ������������κ��˶����ֵ�����Ȼ�����ӵĻ������پŷ־��嶼��ȷ�����������ӵ���Ϊ��Ҳ���پŷ־��嶼ֵ��������Ϊ��������������ˣ�ʣ�µ�һ�塪�����˾��������ķ��ӵı���еġ������ٷ�֮һ������ʱ����ᱻ�������Է����Ը������Ը��У����ձ���Ե���������һ�µļ�С���֣��ı绤����Ҫ��������������ô˵��Ҳ������Ϊ����ӹ������ܡ������������������ȫ�𱸡���ʵ����ʹ�������˰ѷ��ӳ��Ϊʥ�ˣ���Ҳ��������Ȼ�ġ��Լ�����û�м�����������������������ˣ����ҽ���Ҳδ�ػ��ٳ����������ˡ�ֻ����������˵���ǣ���ʹ�������ķ��ӣ�����Ҳ��������Ȼϸ������Ҫ����ĵط������ջ������ͷ��Ӽ���������ˣ��϶��о����������е������ֲ������������ų����ջأ������������Ϊ���ּ���������𣿡���
���������ƿ�С��������ʦ˵�����ģ���������������·���ɵ���Щ��ŭ��ͬʱ��Ҳ֪�����ӹ�˵��Щ�����ջ��dz��ڶ��ջصļ��ʡ�����Ȼ��ˣ������Ǹе���Щ�����в���С�Ƶĵط�����Ϊ�Լ��������Զ��һ�㣬��·�Լ�Ҳ�����������졣���������������Ϊ�ǵ�С��������һ������IJ��ܣ��ܹ����Լ���Щ��ֻ��ģģ�����о������¸���������ر���������Դ˸е�����������
�������ӹ������������������ص����⣺��������֪������֪���������ǹ��������Ƿ���֪������������Ƿ�������⡣
���������ӵĻش�Ҳ�����أ�����������֪������Т�������������������������֪�����ֲ�Т֮�����������ᡣ���𰸺��������ţ���༰���ӹ�������Dz��������ӵ�Ȼ����ӹ����ʵ���ͼ����ʼ������ʵ�����ߡ��ճ������������ߵ�����ͼ�������Ļش�Ťת��λ����ĵ�������ע�ķ���
�������ӹ����ڲ�����������½�������·����·������������Ȼ��û��ʲô��Ȥ�����������������������е���Ҫ֪����ʦ�������ۣ����dz�ij��ѯ�������������⡣
���������ӵĻش��ǣ���δ֪������֪������
������������������·�����ķ��ˡ������ӹ�ȴ�е��Լ��ֱ���������˸��ա������Dz���������˵�IJ������ǻ��¡����ӹ����ϵı���������ôд�Ų�����
��������
�������������鹫��λ��־�����ľ�������Ȼ��û�������ֱ治�����벻�͵ĵز����������ɬ�����ԣ������ǻᱻ������������Ի��������������������ĺ�
����������������������֮���������ι�������ʱ�ͺ���ĸ�ֳ������г���������˽ͨ������������˺��ְ��γ��е�����ί�Դ���������Ų����Ĺ�ϵ��
�����������Ǹ�������¶��Ů�ˣ������η���Ҳ�������Ԥ���鹫����λ���˿�ν�����ƴӡ���õ��鹫��ʶ����Ҫȡ�����ӣ����Ѿ����˹�����
������������³����ʱ����Ȼ���ٰ������鹫������û���ر�������ݺ�����ʮ�ֲ��죬����������������ѣ����ķ����ӣ�����Ѿ�Ϊ�ֵ��ߣ����Ȳμ���С�������ˣ�������һ������
�����������ѣ�����ǰ���ʺ���������ʺ��������ӡ��������б������֮�������ٰݻ���ʱ���������ϵĻ��嫚Ȼ���졣
���������Ӵ�������������·�Գ�һ��¶�ǵIJ������顣��ԭϣ�����ӻ��������Ū�����Ҫ����֮�����ġ���Ȼ��������Ϊ���ӻ���������Ȧ�ף������þ��Խྻ�ķ����������ۻ����Ů��ǰ��һ��ͷ��Ҳ�����˲���ġ��ͺ��������������ˣ���������ı��汻ӳ��ʲô����֮���Ӱ�Ӷ����֮Ψ�ֲ���һ����
������������һ������·���Ͽ������;����ܸɵ�ʵ�ɼұ��ڶ��ӵ��Ǹ����Ӳ��ܵ�ʲôʱ��Ҳ�����ϳɣ��������Ǻ�Ц������Ϊ�ѡ�
������һ�죬�鹫���������һ��ʹ�ߣ�˵����Ҫһͬ�dz�Ѳ�ǣ�ͬʱ����������̡�������Ȼ�����·������̳����ˡ�
��������λ���Ӹߴ�һ����������ү�ӣ���Ȼ�鹫�����������߱Ϲ��Ͼ�����������ȴ����ʮ����Ȥ�����������Լ�ȥͬ��Ѳ�Σ���������д�����
�����������˼����鹫���������棬��Ҫһͬ�dz���ȴ��Ũױ��Ĩ�������Ѿ������˳��ڡ�û�п��ӵ���λ�����Ӵ��Ų��������Цע�����鹫��
����������Ҳ���IJ��죬�����Թ����鹫�ľٶ����鹫�����ش������۾������Ƕ�����ʲôҲû��˵��ֻĬĬ�ذѵڶ�����ָ���˿��ӡ�
�������������������������ǡ�ǰ������������������������鹫������������ӷ��˺���ĵ����һ��������Ŀ��������������Ķ���ţ���������εĿ����泯ǰ������Ȼ��������;�����������˵���̾Ϣ�����˰���üͷ��
��������Ⱥ�����·Ҳ�������⸱�龰������ղŽӵ��鹫ʹ��ʱ���ӻ���ı��飬�����絶�ʡ�
��������ʱ����Ū�������������ô���ǰ��������·���ɵô�ŭ���ս�ȭͷ�ֿ���Ⱥ��Ҫ���ȥ������ȴ���˴ӱ���קס�ˡ��������ۻ�ͷ��Ҫ���Է�˦����ԭ��ȴ���������������ˡ�ƴ��קס��·����������˵��۾������������ˮ��������������·�����������˻����ȭͷ��
�������ڶ��죬����һ���뿪������������δ���õ����ɫ��Ҳ�������ǿ��Ӵ�ʱ�����ĸ�̾��
������ʮ
������Ҷ���Ӹߺ�ϲ���������ھ���������������������������ÿ�������������м䡣���ϵ�������˵���´�ϲ������һ�շɽ���Ҷ�����Ҫһ���Լ��ij���ߡ����������ΰ����ͷ������ڣ���β��������ǰ��Ҷ����������ս������Ķ��ߣ�ʧ�����ǣ�����������
���������ÿ��ӵ�������ȴ����������ʵ�������һ����Ҷ������֮������ʵ�Ŀ��Ӷ���������˵���ڸߴ��ˡ���Ը�⽫���ӷ�Ϊ�����Ĺ��ң�Ҳ�������˿��Ӽ������ӵĹ��ҡ����ǣ�Ը��ʵ�п������ߵĹ��ң�ȴ��һ��Ҳû�С��ڿ�����ܱ������裬���ι���鳼�Ⱥ������ѵ������ϴ�ͽϮ�������ľ���Զ֮������ѧ�ߵĶʼɡ����͵��ż�����Щ���ǵȴ��ſ��ӵ�һ�С�
��������������������Ҳ�͵����ǽ��в�ֹ���д費������֪ƣ��ش�һ������Ư������һ�����ҡ���������ľ���ܣ�ľ�������ݺ�����������仰���ڸ�Զ���������Ǻ���֮�ԣ�ʼ�ջ���Ѱ��Ϊ�����á����ң�Ѱ��Ϊ�����ò���Ϊ���Լ�������Ϊ�����£�Ϊ�˵�������ʦ�͵�����ȫ���������ĵ���ô�롣����ʱ��Ȼ���죬���ʱҲ����ϣ���������Dz���˼���һ���ˡ�
����������һ���ܵ����룬��ǰ������������ʱ���¹��Ͳ̹��Ĵ���������ټ���ͽ������������Χ������;�С�������Ϊ���Ŀ���Ϊ�����ã����Թ�������ݺ���
���������ͽϮ�������ǵ�һ�Σ��������������������١��������жϣ��������촶�̲��𡣼�����ƣ�����������˲����������ڵ����ǵ������ͻ̿��У�Ψ��������Ȼ��������������һ���Ҹ費ꡡ�
��������·����������ƣ�������ӣ��Դ�ŭ�ݵ��ߵ������Ҹ�Ŀ������ߣ��ʵ��������Ӵ�ʱ�Ҹ裬�������𣿡�
����������û�лش𣬲��ҵ���Ҳû��ͣ�¡�һ�����ˣ�������˵�������ɰ��������������㡣���Ӱ�������Ϊ�˲�������С�˰�������Ϊ�������˼ɡ��Dz��˽���ȴ�����ҵģ���˭�ҵĺ��Ӱ�����
��������·��Щ���������Լ��Ķ��䡣���������������У���Ȼ��Ϊ�˲����������֣�������������˷��ӵ����⣬��ʱ��ϲ��������ִ�����������������ӹ�����֮��ͣ������ظ������顣һ�Ե�����Ҳ��ʱ�����˼�����ƣ������������ֺ��ļ���֮���С�
������ͬ�����ڳ²�֮��ʱ��������������Χ����·�ʹ������Ļ���������Ҳ����ʱ�𣿡���Ϊ�������ʦƽ�յ����ţ�����Ӧ����û����ʱ�ġ�
�������������̴����������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