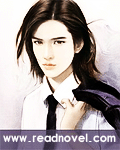岁月不在服务区-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日子来机场都是送人和接人,此时我才发觉空姐都换了新的制服,不是李海南最喜欢的那个款式了。
这次回家我没有通知父母,想给他们一个惊喜。我家在一个小镇,一个人口只有十万左右的小镇,没有任何资源,不靠近交通要道,我爸在粮管所工作,农业税取消以后单位就摇摇欲坠,我妈在广播站上班,从事着与广播毫无关系的事业——织毛衣。
在石家庄转了火车,大概三个半小时的路程,跟几个莫名其妙的人坐一张桌子,还好我的票靠窗,可以看看外面风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铁路周边的村子都被粉刷过一遍,炊烟袅袅,宁谧让人神往。偶尔一些靠近铁路的墙面会写一些广告和标语,如,肥壮壮开胃饲料,吃了还想要。少生孩子多种树。前列腺问题,找康乐健。
最有趣的是,在这个村庄你看见一句话:拖拉机禁止载人。
在下一个村庄,又看见一句:拖拉机禁止向乘客乱收费。
由此可见,国家最低领导人村长还是有点权利的。
身边的哥们一直在用手机玩象棋游戏,那山寨机,屏幕有巴掌那么大,我偶尔也瞟上两眼,他几乎不思考,直接走,然后一直按悔棋,我心想要电脑能出来非把他弄死不可。
这次挑的出行时间还真挺不错,春运刚刚结束,大家都恢复了工作,基本上属于一年里交通淡季。
下了火车就剩最后一程了,此时离家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得坐小巴士,我买了票爬上车,只剩下最后一个位子。
六十八
那车出去了五六公里,我四周一看,真把我吓坏了,身边坐着个女的,气势逼人,整整比我高出一个头,这还是我挺直身子比出来的结果。心想我们男的,压力真挺大的,要长得帅,要会赚钱,最好能家务全包,按摩足疗。现在我还没有一个女的高,真是大大伤了自尊。
惊愕之余,车已经进了修理厂,说我坐的那个位置的轮胎跑气儿,我说我怎么那么矮,后来修车的师傅用千斤顶把后轮顶起来,我立马比旁边的人高出一截。
也许这就是起起落落的生活吧。
下车边抽烟边看师傅换轮胎,旁边一张货车也在休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躺在一个滑板上来去自如,两只手握着不同的工具,满脸机油,脚一瞪就从车头滑到车尾,人站起来肯定也是个玩滑板的好手。
听着乡音,倍感亲切。
这里生活的人民都特别能侃,一天到晚就靠嘴找乐子了,我觉得咱们还都比较勤劳,昆明人连话都懒得说。
司机问换轮胎的师傅:“你这的轮胎也太不靠谱了吧?刚换俩星期就不行了。”
修车师傅被叼在嘴里的烟熏得睁不开眼睛,道:“哥们,咱这是橡胶的,不是坦克的履带,你过来看看,三寸长的水泥钉插里边儿,能不破吗?”
司机若有所思地说:“我也不记得走过这么凶险的路啊?”
终于到了家门前,家里的房子还是上个世纪我爸单位集资的,只有六十多平,在三楼。一眼就看见我妈在阳台上晾衣服,说真的,二十年前我妈也是绝世无双的美女,可岁月真他妈不饶我妈,现在鱼尾纹疯长,都是为这个家操心操的。
悄悄上了楼,摸出钥匙打开门,我妈在阳台喊道:“买到了吗?”
看样子我爸不在,我恩了一声,忽地一种念头涌上来,心想老人家是不是不能多受刺激了。赶紧藏在门后,想了又想,现在处境极为尴尬,出来怕吓到她,躲着也不是办法,犹豫再三又摸到家门口,想先下去给她打个电话。
手才摸到锁上,我爸从外面打开了门,呆呆看着我,大叫:“北方,怎么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呢!”
我妈闻声喊道:“北方怎么啦?”
那天晚上,我们彻夜长谈,我妈的主题是关于我要不要回来找工作,说是让我舅舅找找关系,没准可以留在家里,最为关键的是我不回家她老睡不好。我爸的想法比较随性,说随便我,要是以后要扎根昆明也没关系,反正他们老了去南边养老也挺不错。
“儿子,上次你说的那个小陈,怎么不带回来给妈见见呀?你手机里有照片吗?让我帮你参谋参谋。”我妈一边剥桔子一边说。
我无奈地说:“我们分手了。”
二老你看我,我看你,也没搭腔,最后我爸说:“吵架了?”
我点点头:“恩。”
“是你的错还是姑娘的错?”我妈说。
“都错。”我说,
我爸躺在沙发上,叹道:“年轻人都这样,吵架还能有都错的时候,我和你妈这么些年,只要拌嘴,都是我错。”
“老北,意思是这么些年我委屈你了?”我妈不服气,追问。
我爸笑笑:“看吧,我又错了。”
聊天的时候,李海南打来电话问我平不平安,我才想起到家都忘记跟他说一声,他说:“我在公司盯着呢,宋军又约我去洗桑拿了,给你个面子我就陪他去吧,把他憋坏了对公司也是一种损失。”
我说:“那你以后隔三差五带他出去放松放松,也算为公司出了份力。”
李海南嘎嘎大笑:“必须的。”
第二天下午,他又发来短信说从公司账户上给我打了一万块钱,让我去给爹妈买点东西尽尽孝心。
大二的时候,我跟旁边宿舍一个叫吴果的男生处得不错,两人闭着眼睛都能尿到一个壶里。吴果经常约我出去喝酒,谈天说地越聊越投机,我这么多年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仿佛都是山寨他的。反正后来我再没遇过这样的知己。
那年吴果交了个女朋友,也带着一起吃过饭,她女朋友同寝室的另一个女生被李海南玩玩丢了,伤心欲绝,整天哭哭啼啼,茶饭不思。吴果得知此事拍桌子打板凳,吃着羊肉串就骂街。
要不怎么说志同道合呢,我想得跟他真差不多。李海南这孙子还不是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那张破嘴碰到雌性动物上去就是我爱你,喝完酒涂点意识流散文,骗这个骗那个,声称睡过二十九个处女。这样的人我能待见吗?
可我真的骂不出口,因为他叫李海南。
后来吴果慢慢和我生疏了,我和李海南出出进进的,他看见也不怎么跟我打招呼。
朋友这东西,像馒头和包子,都可以吃饱,但是只有一个心里有肉馅,管饱太容易了,关键是心里得有东西,吴果是知己,但他绝不是我的那个包子。
下午带着我妈上街逛了一圈,给她买了三件衣服,都是平日里她看都不看的专卖店,我拿着剪刀跟后边,试完我满意立马剪挂牌,不买都不行。我说:“您别为我省,我给您买衣服天经地义的。”
后来又买了几件给我爸,经过一个礼品回收的小店,我妈说:“上次你带回来的烟和酒你爸舍不得喝,全拿到这卖了,买了两箱二锅头几条烟还富余好多。”
我说:“那我得回去批评批评我爸。过年不就图喜庆吗?喝点好酒抽点好烟不行吗?”
我妈笑笑:“那你还是批评我吧,主意是我出的。”
在家呆了一个星期,衣服脱了都不敢随便放,一不留神就被拿去洗了,每顿饭都是大鱼大肉,和我爸喝两口二锅头,说说我二叔穿着喇叭裤在自行车后绑个录音机去追我二姨的故事,其乐融融,舍不得离开半步。
只是每天晚上我都失眠,也许是因为长久以来都凌晨睡的原因,也许是我心里真的有事儿。
最赶巧的是马文和夏丽丽的婚礼在我回家的那个星期办了,要不是我打电话约他出来,这孙子也许真不打算告诉我,说是路途太远怕麻烦,我知道以后火冒三丈,酒席间他给我敬了三杯酒,说:“咱们谁跟谁啊?你何必那么在乎。”
我说:“来不来是我的事儿,说不说由你,结婚都不通知我,你准备单干啊?”
后来酒席快散的时候,夏丽丽悄悄跟我说:“他说你太忙,大老远回来让他过意不去,说是在我们婚礼那天晚上给你打个电话,收到你的祝福就可以。”
那一刻,我竟一时无语,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包子吧。
六十九
回到昆明那天下着小雨,我也一样没有通知任何人。
推开家门鼻子忽然酸了,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叫孑然一身。
我也准备换个地方住,这边离公司太远,而且你或许也应该知道,有一种情形叫睹物思人。
殷凡给我打电话,抑制不住兴奋地说:“北方,吴曼她妈病了。”
“什么病?”我问。
“子宫癌,晚期。刚知道就吓瘫了,三天喝了几勺稀饭。”他平静地说。
“那怎么办?”我又问。
殷凡压低声说:“还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
两个星期以后,吴曼的妈真的撒手人寰,吴曼的哥哥吴昊在家闭门了一星期,天天往庙里跑,晨钟暮鼓,清心寡欲。吴曼接过吴母的生意,乱得都翻了天,矿井下三天两头罢工,全国偷矿的流浪汉都奔吴家的矿山去了。
还好殷凡及时接手,凭着一点点小智慧,立马把生意带上正轨。吴曼也不能接受失去母亲的痛苦,成天在家看照片,看她和她妈在世界各地的合影。
林淑的缘一生意越来越好,菜谱一天一个价,一块一块往上加,比开业那会涨了一倍还多。
有时候我真挺纳闷的,钱怎么能如此好赚?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有了个能赚钱的公司。回想这一路,其实都是上帝安排好的,你要是到这一步都没反应过来,估计上帝急了就该变卦了,让你以后的路充满坎坷与曲折。
数星期后,我在XXX找到了一处房子,900一个月,也还不错。
殷凡开着奔驰杀回了昆明,从头到尾焕然一新,手上戴着块江诗丹顿的银色机械表,李海南说这是富足的象征,我说这是富得流油的表现。
那天叫上了俊宏,我们四个大男人聚会了一次,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殷凡判若两人,再也看不到从前那底气不足的样子,看见什么都说垃圾,吃饭前拉开古奇的皮包翻出几包小绿口袋,像是冲剂,让服务员给他冲了喝。
李海南也打开一袋,问道:“什么东西?”
殷凡说:“石斛,听说过吗?”
我们三人一一摇头。
殷凡得意地说:“铁皮石斛,中国九大仙草之一,五千块一斤呢,这包装过的更贵。”
李海南也冲了一包,问:“干嘛使的?”
“有病治病,无病防身。这是我从吴曼她妈那弄来的。”殷凡说。
俊宏叹道:“她妈是不是喝这喝死的啊?”
词语一出,我心跳都加速了,再怎么说也不该拿死人开玩笑,李海南似乎和我想得差不多,也是看看俊宏没说话。
殷凡出人意料地笑道:“命不好喝水都得死。”
那天又一如既往地喝多了,殷凡拍着桌子问我们什么才是成功男人,越喊声儿越大,门口的服务员都乐了。
李海南说:“成功男人就是有车有房有马子,再让父母安享晚年。”
我说:“多挣钱呗。”
俊宏脸色越来越冷,道:“成功男人就是得找个成功女人嫁了,然后安享晚年。”
殷凡也不生气,对我们的回答一一摇头,说:“成功男人就是当他瞪着另外一个人,那人会有被围观的感觉。俊宏,我瞪着你你是不是感觉被围观了。”
他说完放声大笑,俊宏放下筷子,眼冒金光,李海南赶紧拉住他,小声说:“他这人没见过什么钱,别跟他一般见识。”
俊宏压制着心里的火,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根本没打算拦他,他的脾气我们都知道,撅起来几头牛都不是他对手。上学时我们踢球,俊宏总是打后卫,他说他这人不争强好胜,也没那么多斗志,在后场断断球赢了大家都有份。
有一次化生学院约战我们,那天下午我们狂灌了他们4球,有一个球李海南单刀进了禁区里,这孙子一紧张抡起脚朝守门员脸上打去,把他们的门将打得鼻血乱喷,后来一直没能止住送去了医院。
对方剩下的球员当然不爽,后续比赛中动作越来越大,不带球都向你放铲,俊宏在后面也看火了,一碰到对方前锋上去就是犯规战术,在他面前,护腿板根本没用。
结果是我们两个学院在离比赛结束2分钟的时候打了起来,俊宏上去照着他们前锋脸上狠踢,伤得比守门员还惨。那天以后我们四个天天等着被开除,等了两个星期没动静,又怕那拨龟孙心里不平衡去学校告状,最后还是李海南厚着脸皮去约人吃饭,喝了一顿才平息了。
从那以后,我们也再没和别的学院踢过球,关键人再没人和我们玩了。
俊宏刚出包间,殷凡才渐渐止住了笑,说:“至于吗?还他们跟我谈兄弟,我发达了你看他那难受样?”
还好殷凡这人脸皮厚,饭局一结束,李海南接完电话就叫着他去俊宏那玩牌,殷凡居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对赌提不起半点兴趣,推诿了一下回了公司。
七十
后来听说殷凡那晚输了四万多现金,酒也喝得不少,不管拿到什么牌都往里丢钱,从前他多鸡贼啊,不是金花跟一手就开牌。所以说,吝啬这个词语是不属于穷人的,你没钱慷慨个鸟?
殷凡输了,俊宏倒赢了不少,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又像从前那样开着对方玩笑。李海南说,他们不记仇。我说,你不是他们,你又怎么知道。
一天,苏冉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没接,接起来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再没给我来电。
半个月后,她又打过来,我没仔细看号码,接起来听到她的声音,赶紧扯道:“苏冉吗?我电话掉水里的,修好以后所有的名片都丢了。”
她淡淡地说:“难怪上次我打给你你没接。”
“当时在洗澡,后来看见也不敢回,听说回陌生号码会被强行扣话费。你这号码好记,尾数是777,我有点儿印象。”我扯道。
“三小时后的飞机,我要去澳大利亚了,可能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回来。”她说。
我脱口而出:“要我送送你吗?”
她犹豫了一下:“你方便吗?”
我笑道:“没事儿。”
打车到她家门前,她已经下来了,行李只有两个箱子,我说:“你就带这么点东西?”
苏冉说:“好多东西已经托运过去了,其实离开真的挺难,害我从上星期就准备到现在。”
我帮她拖着箱子,问:“你的车呢?”
“那车不是我的,是我舅舅的朋友的,借我在国内用着,昨天还了。”她说。
路上她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听我一直在祝福,我也记不清楚说了些什么,估计都是屁话,只记得她一路都微笑地看着我,眼睛水灵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