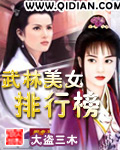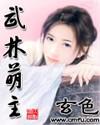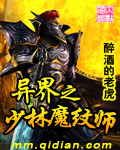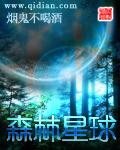卓别林-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除了戏中戏他脸上不化妆,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1952年是他演的新人物与他独创的旧角色的分手时间。
卓别林在1952年春结束影片拍摄后,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1952年9月初,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他抱着很成功的信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放映,观众一致起立向他欢呼。于是,卓别林携乌娜、四个孩子和二儿子雪尼前往欧洲。这,一是乌娜不愿让年幼的孩子们受到好莱坞的某些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求学;二是赴英、法放映《舞台生涯》。他在接见《法国影坛报》记者时,已宣布了访问欧洲的消息。
此前,他已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再入境签证。于是,移民局派了4个人,带了有关他的一尺厚的档案材料和录音机、速记打字机,到他家里来花了3个小时“提出几个问题”:
“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突然问道:“你和别人通过奸吗?”
卓别林对这类非难已领教多次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着,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为了要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在任何国家里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尴尬地说:“并没有这个意思,凡申请再入境签证的,我们都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卓别林反问他们:“‘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于是双方到字典中去查,那人念了出来:“‘与有夫之妇私通’”。卓别林说:“据我所知,不曾有过。”
那人又问:“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可是你始终不曾入美国籍。”老调重弹。“这并不违法呀。并且,我在这个国家里是付税的。”……
后来卓别林反问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许多麻烦吗?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他们吃惊地抬起头,听卓别林说下去:“你们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俄国难民,有一次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临去时患了喉炎。你们政府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候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一周后,移民局在洛杉矶设了一个办事处,来电话问卓别林可否去一趟。结果他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无以复加的招待”,并很快办好半年的签证。办事处主任亲切地把签证交给他:“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他带领全家乘火车赴纽约。从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次横贯美国的旅程,使他摆脱了郁闷心情。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精神上十分愉快。这时,家中添丁进口,已经有了杰拉尔丁、迈克尔、约瑟芬、维多利亚两男两女。
走的那天令人百感交集。当乌娜在收拾行李时,卓别林默默地站在草坡上,用矛盾的目光看着那幢他亲手设计的温馨如巢的房子,他经历过的最倒霉和最幸福的日子的房子。想到就要离开那么美丽而宁静的山庄、花园,他不仅黯然神伤……男仆、女佣、厨师都辞退了,他们与慷慨厚道的男、女主人告别时,都伤心地流泪了……
9月17日清晨5点,他们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汽笛长鸣,巨轮出港后,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回望纽约,雄伟的帝国大厦逐渐留下了空中轮廓,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在烟云霞光中,仿佛是向一个英国艺术家、和一个美国女儿及他们的孩子挥手告别……
孩子们在甲板上尽情欢叫玩耍,卓别林和乌娜坐在帆布睡椅上。想到这次去英国是一家大小,卓别林是那么激动,他感到自己已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仅仅是一个带着妻儿度假的普通人了。浩渺美丽的海洋,荡涤着人的胸襟和灵魂。他和乌娜恋恋不舍地谈起别离的友人,甚至聊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他们就是这样善良宽容地以己之腹度人之心……
当海洋和轮船把博大和快乐带给他们的时候,美国某些人又一次伤害了卓别林: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吃早点时,无线电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播音员还附加了几句话,说司法部长曾发出命令,假如这位著名的演员要返回美国的话,他将被扣留起来。……然而,官方声明说,在调查的结果没判明之前,政府也可以给予临时的入境权利……这意思就是拒绝他再入境了。
是否仍再回到美国,对卓别林来说已无所谓了。从他内心来说,很想告诉那位司法部长麦克和“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们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对别人恶意欺辱,已腻烦厌恶透顶。但是“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舞台生涯》中卡伐罗语)。”卓别林尤其关心的是,他在美国的血汗财产,他怕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去没收它们。因此,他在船上对合众社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回美国去对司法当局的作法进行申辩,说发给他的再入境签证并非“废纸”等。
此后的航行就没有宁日了,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拍来电报。在法国瑟堡停泊时,一百多位欧洲记者登船。卓别林感到烦闷,但对他们的同情作出表示,午餐后接见了一小时。因为是在法国的港口,他特意将法国政府授给他的红色荣誉勋位绶带佩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被卓别林的善良目光、满头白发和庄重安详的神情所感动。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告诉他们: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再入境的诺言,与他离美时频频祝他早归的礼貌态度;以及他仍打算回到他住了快40年的好莱坞去工作。当然,如果能留居欧洲,也令他感到可喜。当有人再次问到其政治立场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我信仰自由,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全部政治见解,这是我的天性。但没有必要把我当作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因为沙文主义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主义。”
当关心他的政治问题的记者们安静一些后,其他记者问起了他的艺术。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不放弃摄制影片的工作。我不迷信技巧,不迷信面部特写的镜头,我深信演技,我深信风格。有些人说我落伍了,有些人说我合符时代,相信谁的呢?”他忧虑地替将来担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属于伟大艺术家的了。它是一个骚动、混乱、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被反动政治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重返祖国,定居欧洲“心脏”
卓别林全家抵达伦敦,滑铁卢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同1921年和1931年一样多,一样热情。穿着节日衣服的
伦敦群众代表,献给他一瓶象征友谊的麦酒和一大束鲜花。他们高呼:
“祝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卓别林是惟一使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回忆的人物。”《每日邮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来支持他:夏尔格的侧影正没入地平线,一个凶恶的饭店老板从一家华丽的私人饭店将夏尔洛赶了出来,老板的脸即“山姆大叔”的尊容。
而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萨伏依饭店,大批的群众聚集在楼下,所有开过饭店门前的汽车,都亮灯、鸣笛,向归来的游子卓别林致意。家乡人们的真情厚意,感动得卓别林热泪盈眶,他对乌娜说:“我没想到还会这样。”
乌娜站在饭店6楼房间的窗口,在卓别林的指引下观赏着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和泰晤士河风光……卓别林在心中说“我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时纽约千万扇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但“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利众生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当然,这种人情味的美,是因为有了乌娜作为前景。卓别林看着在凝视伦敦的年轻爱妻,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他第一次发现,才27岁、与他共同经受了多少考验的乌娜的发束中,已夹杂有一两根银丝。他心里激动地想到,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
《舞台生涯》在伦敦10月16日的首映,是为给慈善事业即为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票价每张25个金币(约折3万法郎)。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出席了典礼,大批好奇的观众包围了奥狄昂电影院……英国报界有的评论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好话,有的文章则用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晚年的高尚的忧郁”,来概括影片的特点。这,自然是美国报界评论的影响所致。
一些朋友们亲切地问卓别林,怎么会招惹了美国某些人的反感。他解释是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同时指出,他并不反对向他发难的美国退伍军团组织。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如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一旦军团某些人员滥用其合法权利,假托爱国者的名义去侵犯他人,这种特权爱国者就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
10月21日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为皇室举行的电影放映会上,接见了卓别林夫妇。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邱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邱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夫妇在10月29日飞抵巴黎,法国电影界各组织的主席、书记(电影编剧、批评家、技师、制片厂职员团体、工会),和一大群记者、影迷到机场迎接。有人告诉卓别林,就在刚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他表示向法国致敬……
在他与乌娜下榻的里茨大饭店旁,是巴黎有名的旺多姆广场,影迷和群众当晚拥挤在那,有节奏地齐声呼喊:“夏尔洛!夏尔洛!”他们希望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饭店阳台上。但饭店大厅的大门开了,卓别林满脸是笑,在那里向涌进去的群众和记者讲话:说他深深喜爱法国,说自己下一步还有明确的制片计划,他既不想扮演拿破仑,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独裁者,他再也不想穿夏尔洛那套老服装了……他最后谈到《舞台生涯》时神情不安地说,这部片子的调子是很忧郁的,又说这部影片被人谈得太多了。最后,他说:“我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
爱丽舍大街的一所电影院里,热闹非凡。法国所有的电影评论家、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去参加《舞台生涯》在法国的首映式,政府的部长们和各国使节也都出席了。连最红的明星到晚了点,也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道上。人们向楼座第一排的卓别林鼓掌欢呼,法国影评家协会主席安德烈·兰格致词时,称他为“第一号公众友人”;让·德兰诺埃代表法国电影工作者,向他表示欢迎。
卓别林出于礼貌,用法语来开始他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让自己用法语来讲话是很困难的,不幸……”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看出他心情有些不安,于是他换用英语说下去:
……我不能不坦白地说,我的心情慌乱极了……我不能跟刚才说话的两位朋友比口才,他们夸奖了我,把话说得太过分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法国人的赞赏,这真使我高兴,也真使我感到光荣。我觉得你们很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出于本能的审美观。……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互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