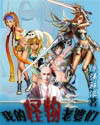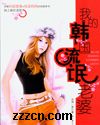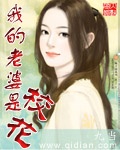˫ǹ��̫��-��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Ʒ����˫ǹ��̫�š�����ʫ����
�������ߣ���ѩ��������
�������ݼ�飺
��������ʫ���������Ǹ�ʱ����͵ģ�����Ǹ�ʱ�����������֣����dz���ʫ������ս����Ϊʵ���Լ�������������顢ǰ����̵ĸ�����������Ǹ���������ƶ�������ơ����䲻�����ĸ߹�Ʒ�£�ȴͨ���ⲿ����Զ���������ǡ�
��������
������
����֣����
����ÿ���˶����Լ��ľ������е��˵ľ������ܷ�ӳ����һ��ʱ���ķ��ơ�
����һ�Ŷ����꣬��������֯����ս�����Ѷ�����װ��������Ҫ�ԣ��������Ƿ���������Լ��ĸ�����װ��������������֮�С�����ʱ����ɽ���Ĺ�����Ա�����Ĵ�����֯���쵼�£��ѿ�ʼ��ʶ������ǹ���ӵ���Ҫ�ԣ����Ǿ����˱���������д�����ҵ��߶����������װ���塪���ԡ����ų�ͻ������ʽ���ֵĴ���������塣������壬��Ϊ�ҵ�ֱ����֯��װ���������糢��֮һ��
�������������Ļ����ϣ���ʮ�����������ɽ��Ϊӭ�Ӻ��ķ�����봨���־����˸����ģ�ĵڶ������塣�������˸��ɽ����������ڻ���ɽ�������˵�����ά��������ǣ���˾�����ɭ��������ı�����Ϊ���������Ľ����ͷ�չ��������������������ս���ڣ�Ϊ�Ը����������Ĵ����տܣ��й������Ϸ��ֵ�������ͬ־���������ڻ���ɽ�������ּ�ǿũ���˶���ͳһս�߹��������տ�һ�������Ĵ����͵ؿ�չ�λ�ս�������ս��ʱ�ڣ���������ɽ����ȼ���˷��Թ������ɵ������һ���ǧ�˲μӵĻ���ɽ�λ��ݶ���Ӣ�µ�ս�����ش�����������صش���˽����������ij�Ѩ������������������ž�����ս���ϵĴ������ӭ�������Ľ�š�
������ʮ���ȥ�ˣ���Щ���Ķ��ǵĹ��º�����������ȴ����ʷ��������������ֻ���ڵ������Ĵ�˵�У�Ĩ����Խ��ԽŨ������ɫ�ʡ��Һã������г���ʫͬ־���µ��ⲿ����¼���������棬����һ��Ů�Ե�ϸ�壬�꾡�����������ʮ�����ﻪ��ɽ����������������װ����Ĺ��̣��������������ˡ�����ս�ѡ�������Щ������������֧���������ǵ�������¡�����������Ǵ���Щ��������Կ����Ǹ�ʱ��������ɫɫ��������Ը�������ʵ̬�ȣ�����һ�����ڲ�ͬ��Ů��������ʫ����һ�����������ɫ�ʣ��뿪��������������֮�ң�������һ�������һЩ����������ļ������۵ĵ�·�������ⲿ�飬���ǻ�֪������ʫ�Ĺ��֮�������������ֺ�ǹ����Ҳ�����Ǵ�˵�е����֡�Ů�����ķ�ò���������й���ͳ�����£�����һ������ʱ������Ů�Ե��������ڶ�ʮ����������������Ŀ������ô���������������ĬĬ������ȥ�������������������������̣�Ҳ���������������
��������ʫ���������Ǹ�ʱ����͵ģ�����Ǹ�ʱ�����������֣����dz���ʫ������ս����Ϊʵ���Լ�������������顢ǰ����̵ĸ�����������Ǹ���������ƶ�������ơ����䲻�����ĸ߹�Ʒ�£�ȴͨ���ⲿ����Զ���������ǡ�
��������һ�Ŷ�����ʮ���ڹ��������ŵ�����Ľ�����̸�����������ǣ������Ǹ�ĸ�ܰ�����ѹ�ȵ�ʹ�ྭ���ͷ����������Ķ�����ʷ�����н������ǹ�����������Ļ�����
������������д����ʮ���ꡢ�������ںͶ����Ǽ�����ⲿ�飬���ڶ��ߡ��ر�������һ�����ù�ȥ�������ȱ��Ǽ�භ������ʷ����������������й���֮���ף��ǻ��а����ģ��Ǵ�������ġ�
����һ�ž��������¶���
��������
��������
������ʮ�����������������ѧ������ı༭�����ͬ־���Ĵ�������λ���������˵���Ĵ�ʡ��Э������֯��������һ����塣�ⲿ�����һλ�г���ʫ��Ůͬ־����������������¼������һ����ҹ������ϸ�����·�������������Ĵ�����ɽ���ҵ��쵼��������װ�������˳�˫ǹ��̫�ţ������ɷ������赣��Ǹ�����ʿ�������ľ������dz��ḻ��������Ҳ��ǿ�������ͬ־�������Ҫץ�ⲿ���ӡ�һ������������ҵ��˳ɶ������������������ߡ�������ʫ��Ů����������Ů�������Ҿ�����������ɫ��������������ץ��С˵���鳤������ͬ־�����α༭������������ִ����д���һص�����֮������ɳͬ͡־������Ҳ̸�������ʫͬ־���¼������Ƿdz��ɵġ��Ժ�������ͬ־Ҳ��ε����ɶ�����������������ͬ־���������й����ˡ�
�������Dz��ã������塱�˶���ʼ�ˣ��������ǡ��Ļ�������������ǽӵ��ü����״�ţ�����һ���Գƻ�������赵�ͬѧ��˵�������ɽ�ǵ��ġ����ˡ�����ʿ�Ǽٵģ���˵����ɽ�λ��Ӹ��������ڣ���������Ҳ������۵㡣һʱ�����ⲿ���ͳ���ʫͬ־�����ǷǷǣ��ֵ÷�����������ô����������������˵������ͬ־����Ƿ߳ɼ�������ȥ����ɳͬ͡־�ڡ��ĸ��Ҳ�ܵ�ǣ�������ĸ���ڣ�ɳͬ͡־���˱������ֺ���̸��������飬é������Ҳ��ר�������ʹ��ⲿ��壬���ǵ�ʱ�������鱾��ûŪ����������ܳ��棬ֻ�еȴ����ᡣ
����һ����ʮ���ȥ�ˡ����ĸ֮���Ĵ��ĵط�����֯�Ƶ���һ�в�ʵ֮�ʣ��Գ���ʫ�ĸ���������ʷ���˹��������ۣ��������ͬ־Ϊ��ʿ���������˵���ǵ����ﱲ�ѽ������������һ���ɶ��Ժ�ǿ�Ĵ�����ѧ��Ʒ���������й������������Ϊ�ص�ͼ���Ƴ����ҵ�����dz����ˡ�����ʫ��һλ�dz������Ů�ԣ�����������ԣ��������������ũ����һ�����˶�ʮ�������װ�������ɷ�����֮����Ȼ�¶���ĸ�ָ������ڷdz����ѵ������´Ӳ���Э��ͷ�����Ǻܲ����ġ���ϣ�����Ķ��������ر��������������Ƕ���֮���ܹ������ܵ�������������ϡ�
����������ʷ�������պ���
������������˫ǹ��̫�š�����ʫ������
�������ѷ�
��������һ���������Ĵ����µ��ĵ��¹�������ͬ־��������ʮ���ĩ����ʶ�˳���ʫͬ־���������ĺ�����һ�������Ϊ��ʫ���������������Һ���������ȫ��һֱ���������ܵ�ս�����꣬Ҳ��������Ϥ������ͬ־һ����һֱ��ע��������������ʮ�����ֵĿ�������¼��
�������ڣ���Щ�����������ϣ����������ĺ��д�ɴ�����ѧ�����ˣ���������壬�����Ķ�����������������ƽ��������
����һ�Ŷ����꣬�ҵ���������ʱ�ڣ�������װ���������������Σ��������������������֪ʶ�����������Ȼ�����˵���֯����Dz���������ӳ���ʫ�ص����Լ��ļ��硪����������ɽ�µ������ء��������Լ�������������һ�����ص�������װ��Ȩ����ͬ־��һ��ץסȺ�ں���С����ʹ�����������������������Կ����������ط�����Ϊ���ĵġ�������������壬���Դ�Ϊ�����������ҵ�ֱ���쵼�ĸ�����װ���ڼ����ն����ѵ������¼���˶�ʮ�����λ�ս���������Ĵ���ȫ�����Ǻ����ġ�����������ø�����������֮���ì�ܣ��ƶ�������ս��ս����ǣ���˷���������Χ�ˡ�����Ĵ���������Ϊ���¸������ݵصĽ����ͷ�չ��������Ҫ�Ĺ��ס������ӵĶ���������ڴ�һ�������ڵ�����������֪ʶ���ӣ��������ҵ��ܳ���ģ���ȷ�����͵���Ⱥ�ڰ��������䣬ͬʱҲ������һ������ǿ�ĸ����Ǹɣ����ǽ���������Ⱥ��Ѫ����ϵ������������ڵ��˵�Ѫ����ɱ��ҧ�����ؼ��������ʹ����ɽ��������������ս��Ҫ�أ�һֱ��Ϊ���ڵ����ĸ�֮�ص�һ��������
���������ſ����Ȿ������ǣ�Ҳһ��������ʫ������ڲ�ͬ��Ů�������������������ɷ�����������ϸ�����·����������ȥ�����Щ����Ҫ��Σ�յ�������û�о�����ս����ȴһ����һ�ν�������֮���⣬ð��ǹ�ֵ���ʤ����������û�������⣬��Ϊ���λ��ӵ����棬������װ�꣬�����ϰ壬�������У�ÿ��Ҳ�Ǵ��������˼��ν�����������������û���������������п�չ������ʽ�Ķ�����������ذ��������ɷ�ͺ��ӣ���Ϊ�˸���ȴ���ڹ�����롭����Ϊ�ɹ���ǵ�������������λ�����������ɢ�������ϼ���֯ʧȥ����ϵ������£�������ʧȥ���˵ľ�ʹ����Ȼ���ϻ���ɽ�������ٶ��飬����Ҫ���ɷ�δ��ɵ���ҵ���е��ס�
�����������������Գ�Ӣ�۱�ɫ��������ʫ�ľ�����Ϊ����������һ��ΰ��Ů�Գɳ����㼣��ҲΪ����������һ�ʱ���ľ���Ƹ�������ʹ����һ���˽����ǵ���������е�һ����Ҫ�Ķ�����ʽ���˽ʱ�Ĵ�����ỷ���ͷ������飬����Ҫ�����˽�һ��ΰ��ġ���ߵ��ˣ���Ϊ���ǵĵ��������������˶��Ժ���
������ޢ�껪
�����������������죬�ؼ��꽭���ϣ����ϴ�����ʤ���͵���һ�������ص��ء����꽭������������ӣ��ֱ������ص����ߺͶ��������������ŵı�����ض���ͻȻ¡��Ļ���ɽ��������ص�ƽ�Ӻ�dz�������ʢ�����ȣ�����ġ������ס���������͢��Ϊר���ʵ��϶��ԵĹ��ף�һֱ�DZ����˵Ľ�������Ϊ��ʳ���㣬��ȻҲ�������ͼ�Ѽ�ݵ�֮��ĸ�ҵ���ڿ���˼�����Щɣ�ϣ���Щ��ϯ��ϯ������Ҳ�������ȥ�����Ϻ����ع㰲����Ļ���ɽ�ϣ���ľ��ï�������϶룬ɽ�ϲ�������������ҩ�ģ�����ú̿��ʯ�ҡ���Щũ�����������������˵����ٶ���֮������죬�پ��������������ذ��ĸ�ʡ��С���У�����˳�˴������ˮ�ƣ������Ӱ��ߵ�����С����Ϫ�������������������첻�������·�̡�
����������������ȥ����������ɽ���������������ƶ�ĸ���ȣ�һֱ���Ŵ��ɽ�������ǵ���Ҳ���Ǵ�����һ���ص����أ������Щ�����۲�����֪��ʲôʱ��ʼ�����ˡ������ء������ơ�
������Ϊ���㲢�Ҳ�ƫƧ������Ҳ���˲ġ�һ�����˹��ſ��ŵĻ��ᣬ���СС��ʿ���ӵ��DZ㲻ֻ�����鷿�����Щ�˹����£�Ҳ�����죬�����ţ������ڡ��Ͼ����Ϻ����������������ձ���ѧ���졣����֮��Ҳ�о���������٣������½����������õع���ҫ��ģ�Ҳ�й������룬��־����ɣ���������ڼ��罨һ����ҵ�ģ���ȻҲ����;��˳����ѧ�չ��ҹڹ������о�����ġ������ַ��������ഫ�����˱����ͳ���Խ����ʢ������
���������س������һЩ�������Ŀ���ʡ�Բ�˵�������ҵ�¥��ȴ�dz��︾���֪�ġ�����һ�����е����ɵĴ�լ�ӡ�����������峯�ĺ��ִ�ѧʿ�����Ź���ʡ��������Ϊ�˳���ר������һ������Ժ���Լ�����λΪ���縸�����˹�ʵ��������Ҳ��˳����ڵط��Ϻ�˵�����������ҡ����ǽ����أ������ͥ�㲻������������������֮�����ּ����Ŀ���������������Ҳֻ���˸�����ŵ����֣���������ȴ����㹦��Ҳû�У��ͷϳ��˿ƾ١����¼�����Ȼ��Ӳ���������ŵڵ����ɣ�ȴ�����Ե������ˡ�
�����Ҿ���˳�����ľ�Ҳ�Ͳ��ã���������֮ʱ�������ۿ���Χ�����ߵĶ�Ů�����ǣ����ⲻ��Ϊ���ǵ��ġ�����������˵û�й�����ȴ�ô�����Щ�������µļҲ����������˲����ĵ��������Ǹ�Ů�����뵱�����Լ�Ϊ��������������˸����żң���������֮�����ӱ��������ij¼Ұ����������Ĵ�������Ů���ĵؿ���Ƣ��Ҳ�ã����п��˸�ҩ�̣��Լ���ҽ����������Ҳ������ȥ�����ϳ¼Ҿŵ��֣��Ǹ����壬����Ķ࣬���ٵ�Ҳ�࣬�˼Ҷ�˵�Լ���Ů���ͽ��˸�����������츺��Ը��û�뵽����֮�Լ����������ܿ�Ͱ�ټ��һ�ݼҲ��ܵþ��⣬����ǰ��Ů��Ҳȥ���ˣ����������Ů�������ĸ����ӣ�ȫ��Ϊ����Щ��֯���������Ҳʵ�ڹ��ü��ѡ�
�����뵽��Щ�����˳�̾һ�����Ը�����ӰѼ�����·�������ʰһЩ����Ů������ȥ��
����û�뵽�Ա�ͻȻð����һ��С����������������Dz�Ҫ����������Щ���⣺��Ϊɶ��Ҫ����
������С����̧ͷ����ĸ�ף�����˵����������˵�ģ�����Ҫ���Ӳ������Ҫ�������ʣ�Ҫ���˼ҵĶ������ͻ����˼ҿ����𡣡�
�������˻軨���۾��͵�һ����һ�Ĵ��أ�����˵�����á��á��ã�����־�������һ���г�Ϣ�������ͽ��������������飡��
�������С��������ҡ�����һ�š��������ģ���ʱ��ֻ���߰��ꡣ
�������游ȥ��֮��ĸ��������ס�����Ļ��������������������ͯ��ϱ���������ŵ����첡�Ĵ�磬����ǧ���ټƴ���ЩǮ�������͵����żң��ڴ�˵��շ�������ѧ������Ǹ�����ˣ����Ͷ����д��СС���ĸ�Ů�������궼���Ҳ�ࡣ������ĸ�Ŀ��ģ�ѧϰ����Ŭ�����ɼ��ã�����һ�뵽�Լ����������һ�ּ������µĸо��������������������裬���Ҹ���谮��������˵����������Ů�������ã�������С���������Ե��Եÿ��п࣬��Ϊ�����ˣ�Ҫ�����˸�ʲô�¿ƣ��Ҽ�������˵�����ͻ����˸�Ů״Ԫ�ء�
�����������ų軵���ң�������һ�����żң��͡������췴������������������ɭ�ϵĴ��ͥ����һ�ж������ס�
������ʱ����Ȼ�����������Ѵ��ձ����������������ص�˳�죨���ϳ䣩���ˡ�����ᡱ������ɨ��ªϰ�������س�����Ȼ����Ů���겻��ͬϯ��Ů����ʮ����ž͵����������ij��Σ�����֮����Ȼʢ�С��ҽ����żң�����ʮ���ˣ�����һ˫���㡣���˼�һ����˵�����������˼ң�Ů��������û�й�أ������˼һ�˵����������ˣ���û�н̺á�˵�ž��þ����ó����IJ����Ӹ��Ҳ��㣬���˻������߷��ϣ����ҿ�Ҳ�ã���Ҳ�ã����Dz����ҡ�����С���ԣ��ڼ��ﶼ�Dz����˹ܵģ������ܹ��������һ��֮�£�����������һ�Ѽ���������ǿ�в����ˣ������Ҿ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