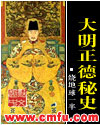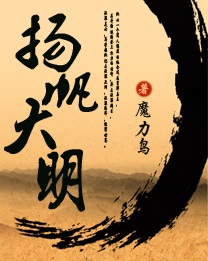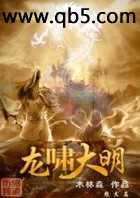大明王冠-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昏笑了笑,“那我们来谈谈。”
讲道理?
我真不怕你们,哪怕你去叫上已故的方孝孺先生来,我一样说得你们哑口无言。
道:“先说一事,太祖驾崩之后,我大明江山可存在内忧外患?”
许吟迟疑着点头。
内忧是有的,比如明教、白莲社等社会团伙,还有彭和尚的残余势力,外患也存在,蒙古帖木儿尚有兵马十数万,虎视眈眈意图反攻大明。
黄昏继续道:“但朱允炆登基重用齐泰、黄子澄等酸儒,须知酸儒误国!之后一系列措施亦是抑武扬文,打压武勋集团和武将体系,这就失了军心,加上太祖屠戮功勋武将,导致军中无名将,后期基本靠朱棣撑着北平,朱允炆一旦杀了朱棣,短期内不见危害,可若是爆发战事,岂非又是元末之天下大乱?”
许吟不语。
这是事实,他无法辩驳。
黄昏又道:“再说一点,朱允炆登基之前,曾对太祖说过削藩之事,说对诸位藩王,先怀柔,若是诸藩王不服,再起兵锋削之,我没说错吧?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提及过。”
许吟点头,这也是事实。
黄昏娓娓而谈,“可朱允炆登基之后怎么做的?太祖尸骨未寒,朱允文便矫遗诏,不允许诸位藩王回京奔丧,随后找个由头废了周王,把周王一家赶到云贵边境去做人猿泰山,又软禁齐王、代王,皆废为庶民,皆着诬陷湘王谋反,湘王能怎么办?为表清白,举家自焚!许吟,这可都是朱允炆的亲叔叔啊,那么多人,说死就死了。再说回来,朱棣一开始是想靖难的吗?朱允炆要他交兵权,朱棣交了,还把朱高炽等人送到京城做人质,甚至被逼得装疯,可朱允炆放过他了吗?没有!朱棣没办法,只能靖难,说什么蓄意谋反,可你也不想想,朱棣若是蓄意谋反,会在朱允炆要拿他之前,才被主动投靠的张信救下,仓促间带着八百人造反,带领八百死士造反……你觉得哪个藩王会如此随意,这不是被逼无奈?”
黄昏真不是替朱棣洗白,都是史书记载。
不过……有些事不可尽信书,关于永乐和建文这对叔侄的事情,可以信书,但不可尽信书,毕竟后来的史书都是王者之辞。
朱棣很可能会抹黑了建文帝。
何况明史是清朝编撰的,清朝那群帝王,能同时抹黑这对叔侄,自然乐意的很,所以朱棣真不一定是被逼的。
根据史料推测,朱标死后,朱棣确实对帝王充斥着渴望,且他优秀的能力人尽皆知,这给了朱允炆太大的压力,导致朱允炆不得不出极端手段。
所以黄昏只看结果。
不论对错。
朱允炆错不错没关系,朱棣打造出永乐盛世,朱高炽和朱瞻基打造出仁宣之治,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尊重事实。
许吟一声长叹。
他不知道如何辩驳,他也不是读书人,讲道理肯定是要输给黄昏的。
最后,黄昏再次深呼吸一口气,压抑着胸腔间的痛楚,一字一句的道:“我在贵池县对叔父黄观说朱允炆没死,是缓兵之计,许吟你自己想想,朱允炆若是逃出了应天,朱棣这江山能坐得如此安稳?”
许吟抬头,直视黄昏。
黄昏一脸正色。
许久,许吟才低头,眸子里满是痛楚。
原来如此……
黄昏见状心头暗喜,面上却淡然得很,道:“这件事你告诉了景清,也告诉了刘莫邪?”
许吟摇头,“只告诉了景清。”
黄昏陷入沉思。
这就说得过去了,景清知道朱允炆没死,可这种事他也不敢告诉其他人,万一走漏风声被朱棣知道了,朱允炆没死也得死。
所以景清先利用自己设计离间朱棣父子。
失败之后又制造上元大火案,皆是步步杀机,一旦朱棣出了事,蛰伏的建文帝现身,自然被众人迎回紫禁城复辟。
自己小看了这位御史大夫。
之前还笃定他做不出上元大火案这种事情,现在看来……读书人,真不可小觑。
看向许吟,“景清杀我,你不知情?”
许吟点头。
黄昏心中微暖,倏然厉声道:“长街奔马,丧命者众,许吟,这是你想看到的吗,那些个冤死马蹄之下的人,你可曾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
一字一句的吼道:“他们,就该死吗?!”
许吟想起长街奔马的那一幕幕惨状,内心又如火煎,痛楚至极,仰首一声轻喟,“又能怎样呢?”
旋即低语,“景清已去,那我许吟以命偿之罢。”
话落,锵的一声。
长剑出鞘。
黄昏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许吟的手,“你自刎了,死在奔马之下的人就能活过来?”脑海忽然炸裂开来,又厉声道:“你说什么,景清已去?我昏睡了多久!”
许吟本能的答道:“一日。”
黄昏松开许吟的手,转身就向外狂奔,临出门时回头说道:“留着你的命,用你的余生忏悔,为在世之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才不至于让昨日的血白流。你既执剑,且赠你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匆忙出门,撞倒吴溥,丢下一句吴叔见谅,狂奔而去。
必须赶去紫禁城。
第七十三章 兴亡皆是百姓苦何不窥盛世
吴溥抬起手,又放下。
一句“有伤在身不宜疾行”,到了咽喉又吞了回去,望着奔出院门就开始捂着胸口的黄昏喟叹一声,何苦呢。
你不欠朱棣的啊。
君子非礼勿听。
吴溥是个君子,自然不会躲在墙角偷听谈话,可昨夜长街奔马案,死伤十余,还涉及到他最青睐的晚辈黄昏,更有他亲生儿子,由不得他做一回小人。
走入房门,坐下,望着许吟。
许吟有愧,不敢回看,只是侧首望窗外春光灿烂,心间却是乌云绵绵,黯然道:“与弼是个好孩子。”
吴溥颔首,“我教的。”
能不好?
许吟又道:“他的伤没事吧?”
昨日为了从奔马之下救出黄昏和吴与弼,许吟长枪横扫在黄昏背上,落地之时吴与弼在下,当了一回肉垫。
受伤不轻。
也幸亏如此,不然黄昏的伤势将会更重。
吴溥又颔首,“还好。”
语气很淡。
但越是如此,许吟的心便越是愧疚。
吴溥的目光落在出鞘的长剑上,许久,有感而发,“关山五十州,男儿带吴钩,人间万万里,侠情千千秋。许吟,你欲与长铗独去乎?”
长铗,剑也。
这一首随口而来的不算严谨的小诗,先说男儿壮志,带吴钩而卫山河,怀侠情而平人间不平事,最后用一句话质问许吟,你要和长铗一起离开这人间,辜负一身才华么。
很读书人的说辞。
许吟唇角浮起苦笑,“事已至此,我还能怎样。”
吴溥沉默。
此事不能论对错。
景清做到了无数人做不到的事情,朱棣入主应天之后,像景清这样的读书人很多,但愿意、又敢这么做的,能有几人?
自己就做不到。
但景清该死,为一己之心,竟丧心病狂的长街纵马致无辜枉死者众。
说道:“黄昏临走前那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觉得甚好,许吟,你可曾自诩侠义?”
许吟苦笑,“我本侠客行。”
许吟本起于江湖,后入军伍,被徐辉祖赏识,靖难之后,徐辉祖知道朱棣会清算,所以提前让许吟回徐府当徐妙锦的护卫。
徐辉祖不笨。
有姐姐徐皇后在,徐家的人一个都不会死,但许吟留在军伍,再无前途。
又补充道:“我所做之事,不是为国为民?”
难道不是侠之大者?
吴溥起身,推开窗户,让春光肆无忌惮的照射进房内,眯缝着眼盯着窗外的新柳,感受着街上的熙攘声,轻声叹道:“你看看这应天繁华,这泱泱黎民,可曾需要建文皇帝再起一场兵锋?兴亡皆是百姓苦,可家国动荡之苦,无人愿再承之。”
宁受苛捐杂税,不承荒烟蔓草。
须知当下,已是盛世可窥啊!
转身看向许吟,“大明内忧不断,外患蒙古帖木儿虎视眈眈,若是再来一场波及全国的复辟之战,百姓又将生灵涂炭,许吟,这是为国为民?”
许吟语结。
他连黄昏这个假读书人都说不过,何况吴溥这个真正的读书人。
吴溥上前,将长剑归鞘,递给许吟,拍了拍他肩头,“与弼也醒来了,他让我来谢谢你。”
说完出门,留给他空间自我审视。
许吟本质不坏。
吴与弼醒来后说过,是许吟救的他和黄昏,按照刚才在门边听到的事情推断,景清是真的想杀黄昏,这件事瞒着许吟。
而许吟不知何故又恰好遇见——想来应是徐妙锦吩咐他保护黄昏。
所以他明知是景清的计划,还是出手了。
黄昏跑出院门,发现自己这伤后的身体根本跑不拢紫禁城就要跪,可吴溥家没马——封建王朝,一匹马就是一辆车。
贵着呐。
但隔壁胡广家里有马。
问题来了。
黄昏不是套马杆的汉子,不会骑马。
站在门口茫然四顾。
看着天穹春日,估摸着时辰,心中焦急万分,时间不等人,若是再这么拖延下去,天下没人阻挡得了那件事的发生。
不论景清成功与否,都是最坏的结果。
吴溥走了出来,“怎么了?”
黄昏苦笑,“需要一辆马车。”
可一时之间去哪里找马车,马是小车,马车就是豪车,这里虽然是京畿,豪车确实很多,但也不是随处可见。
吴溥沉吟半晌,“我去借胡广的。”
胡广很抠。
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给,何况今日胡广去上朝了,他妻子倒还算好说话。
黄昏依然苦笑,“咱俩都不会骑马。”
吴溥个读书人,也不会骑马。
身后传来声音,“我会!”
许吟腰配长剑,没有提那柄长枪,站在门口,神态憔悴,眸子里倒是平和,“我想为自己做的错事弥补。”
黄昏大笑。
骑马奔行,黄昏依然被颠簸得难受,好不容易捱到洪武门外,对守城的京营士卒吼道,有急事要当面觐见朱棣。
守城的小将领也是固执。
说陛下有过旨意,你是同进士出身,可以去见圣,但紫禁城内可不许奔马。
黄昏翻了个白眼。
没敢耽搁,下马之后急忙前行,前往奉天殿。
这个时候,还在早朝。
……
……
奉天殿。
朱棣身着绣“十二纹章”的黄色通天冠服,大马金刀坐在奉天殿中,目光俯视着殿内众臣,在殿门之外,臣子两分,一直绵延到奉天殿外的大广场之中。
京官是很多的,加上一些地方官进京汇报工作,杂七杂八加起来,上百号人。
臣子虽多却寂静无声。
朱棣很满意这种状态。
很爽。
泱泱神州,谦谦人才,皆在吾罄。
扫视完众多臣工,满堂臣子之中,不见绯色朝服,心中略略舒缓了口气,钦天监那边之前说过,近来帝星犯急,需要提防红色,可这种事也不能告诉臣子,说老子最近看红色不顺眼,你们上朝的时候别穿红色朝服。
帝王如此迷信,影响不好。
有条不紊的处理了大事。
实际上大朝会上的朝政大事,早就在常会,或者寻常时候就和六部等中枢部门的大佬们商洽好了,何况现在又有内阁帮忙论政,大朝会仅仅是宣布大事如何处理的而已。
第七十四章 透心凉心飞扬
又决断了一些外地官员启奏的事情。
时候不早。
到了退朝的时候,朱棣却没有让狗儿宣退,看向众多臣工,问道:“应天府尹向宝可在?”
向宝出列,手执朝笏,躬身道:“臣在。”
朱棣道:“朕听闻昨日京畿城中,出现一奔马失控事件,伤亡者甚众,府衙那边可有查明实情,是何人所为?”
朱棣很有些敏感。
如果是权贵子弟当街纵马,万一涉及到他想打压的那些个建文旧臣,不妨借机惩戒一下——肃清朝堂,可不是三两日的事情。
向宝大声道:“应天府衙接案之后,迅速奔赴现场查明案情,共有五人当场而亡,九人重伤,皆已安置妥当,其中重伤者,有同进士出身、南镇抚司总旗黄昏。”
向宝的求生欲很强。
涉及到黄昏,根本不敢打任何马虎眼。
朱棣微微点头。
向宝继续道:“肇事者共三人,其中一人逃避追拿时坠河而亡,另两人逃之夭夭,府衙已在全城布防,务必将其捉拿归案,倒是有个疑点,经仵作查证,坠河而亡的肇事者从事着见不得光的营生,生前曾大量饮酒,已是醉酒状态,因此推测,这是一起地下势力聚众酗酒之后无意闹出的一场惨剧。”
朱棣愣了下。
大清早的就醉酒,之后还敢驾马在长街上狂奔,且这么巧合,那么多人不撞,偏偏撞上了黄昏和吴与弼,这里面没鬼谁信。
究竟是谁想杀黄昏。
纪纲?
他不敢。
梅殷?
还不至于。
朱棣沉吟良久,对向宝道:“彻查。”
向宝退下。
朱棣挥挥手,狗儿太监上前一步,尖锐着声音喊道:“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无人出列奏事。
狗儿又喊道:“退~朝~”
所有臣子行却礼。
奉天殿内臣子退三数步后,转身离去——人多,却礼也就意思着一下,若是寻常时候,是要直接退出殿门的。
毕竟这么多人,万一谁一不小心跌倒,那就太伤风雅了。
朱棣也欲起身离去,却讶然发现奉天殿还有一位臣工,手捧朝笏,动也不动。
有些好奇,“景卿家还有事?”
为何不在朝会提及。
景清捧着朝笏微微弯腰,“臣还有事启奏,因涉及驸马,需要和陛下面谈。”
涉及驸马?
哪个驸马?
朱棣的长女朱玉英刚被封为永安公主,其丈夫本在宗人府任职仪宾,随